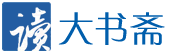正月十五刚过,疏勒城正在忙着军一火交易的同时,洛一阳一正式下达通知,统军府改名为折冲府。 如长安禁苑某个老汉被人逐渐遗忘一样,统军府这个名词,也算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贞观十七年新增折冲府主要从关一内一道转移到了山东、西域以及剑南边陲,裁撤合并的军府数量相当多,主要集在江淮。
因为各种原因的集合,江淮府兵败坏的速度极为惊人,可以说是全国之冠。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里不仅仅有大运河,更有盐场,更有郁洲北地转运仓,大运河和扬子江交界处的扬子县,更是有“王下七武海”的母港。
帝国的地方府兵做点生意贴补一下家用,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了,江淮行书省总督魏徵也是拍过桌子骂过一娘一的:军队一律不许经商,侬晓得伐?!
然而并没有什么一卵一用,这里是帝国最为浮夸最没有严格秩序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西域还要自一由的多。
“巨野县乱一党一”四处流窜,能够在江淮得以生存,这其的道理,也是可见一斑。
秩序遭受挑战,又有惊人的不断发展的工商贸,自然会产生物质和一精一神的双重混乱。
魏徵本来想一咬牙,弄个“严打”,反正武汉也弄过不是?效果斐然,什么香堂会水,根本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魏徵遇到的苦处在于,他手头没人。
是真·没人,连阿谀奉承的杂碎都没有几个在扬州露面。“厘金衙门”附近那些铁了心要钱不要命的总督衙门的多得多,毕竟道理很简单,平头老百姓拿命换钱,从钱老板那里,那是童叟无欺,确确实实可以豁出去捞口热汤。
可魏徵呢?铁面无私啊……
游走在律法边缘的活计,在魏徵这里是讨不到好的。
事情是这么的啼笑皆非,好官清官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束手无策,反而是贪一官如鱼得水,建立了一套葩的“秩序”体系。
尽管这一切,都是因为魏徵“谨小慎微”的错误结果,但正所谓自己约的炮,含一着泪也要打完,魏徵作为一个喷子,这时候也只能选择“冷一茎一”一下。
几次疏之后,将江淮的情况跟皇帝陛下说了说,李董琢磨了一下,觉得江淮要是不搞好,河南和江南都搞不好。
一咬牙,李董开了个董事会会议,结果入席的老面孔,不要说房谋杜断,连长孙无忌都没有。
宰辅位子资格最老的,居然是侍马周。
马周一来摆道理讲事实,先说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了人心的千变万化,再说社会治安要是不能控制,对社会经济是很打击的,毕竟社会生产活动最终也是由一个个工人农民商贾组成的。
于是侍马周表了态:严打是不可能严打的,这几年都不会严打,放任自流又不好,总不见得眼睁睁地看着流一氓们靠暴力做原始积累不管不顾……
说了一堆废话,马周终于说了一句非常有用的话:“臣以为大理寺卿熟悉律法狱断,又善缉捕推理,当能任之。”
然后一帮人齐刷刷地转过头,看着正开小差的大理寺卿孙状头。
孙伏伽本来心里琢磨着下班了去南城喝一杯还不是美滋滋?结果猛地虎躯一震,哎哟卧槽,你们都看着我干啥呀?
“孙卿……”
空灵的声音传来,李董这几年越来越跟神仙似的,太有高不可攀高深莫测的风范。只是喊了孙伏伽一声,让孙状头猛地跳出来:“臣在。”
“依马卿之言,汝有何计策?”
我特么……
孙伏伽余光瞄了一眼一本正经的马周,心说师弟说马宾王是个实诚人,这入一娘一的实诚人是这样实诚的?
他现在想冲去武汉,一把抓住老张的脖子,问他实诚人到底是长什么模样的!
然而老张也是无辜的,宦海沉浮,再你洁白如玉,进去出来,不都得黑么?这又不是他能左右的。
再说了,马宾王当年是实诚嘛。
皇帝提了问,作为大理寺卿,一个法律工作者,你又不能说这特么又不归我管,我不知道。毕竟讲到底,社会治安最后来一刀,不都是依照律法来判刑抓捕流放抄斩嘛。
然后大理寺卿脑子转的也不慢,反正现在开会,随便扯点东西应付应付董事长行了。要是不科学不合理,老子“抛砖引玉”还想怎样?有种你“抛玉引砖”啊,做不到别**。
孙伏伽一想到去年跑武汉的时候,在武汉有大量的特殊“白役”,仿佛好像大概可能差不多是“南四军”那帮废柴们在当差,主要是维持维持治安啥的,偶尔还要集火某些有活力的社会一团一体,物美价廉不说,简直是地方主官的顶级施政小帮手。
于是孙师兄来了一精一神,张口来,只是他绝对想不到,他在跟李董描述某种和武汉警察、城管类似的组织时候,侍马周他仿佛是没忍住,咧嘴笑了笑,要不是勿板挡着,怕不是要被李董瞧见。
当然了,这兴许是马周真的是个实诚人,听到不错的点子,他诚实地会心一笑。
会议结束,满朝武都是一脸佩服地看着孙状头,而廊下寒风,孙伏伽一脸的懵一逼一:你说我一个最高法院院长,怎么要去负责筹建公一共一安全部了呢?
当然了,孙伏伽在李董面前是稍微反抗了一下的,说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这组织部门筹建,没有经验啊,董事长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然后李董说了:这是朕钦定的。
廊下吃饭的时候,马周觉得过意不去,特意把李董赏赐的鸡一腿一一筷子夹到了孙伏伽的碗里,然后神情复杂意味深长地拍了拍孙伏伽的肩膀。
盯着鸡一腿一,孙师兄悲从来,这尼玛筹备公一共一安全部,还要专门打击江淮那帮有活力社会一团一体,这得得罪多少人?
想到这里,孙师兄拿起鸡一腿一,狠狠地咬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