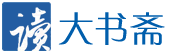虚土 第一部分 虚土庄的七个人(2)
第二年,难得的一场丰收,收获的夏粮足够他们吃到来年秋天,眼看要饿死、瘦得皮包骨头的儿女们,一个个活过来,长个子,长肉和骨架。
这个男人终于爬过我的40岁了。他好像累坏了,喘着粗气。
又一个晚上,她在他身体下面想。
男人就像一个动物,不断爬过她的身体。他的一只蹄子陷在里面了,拔不出来。今天拔出来,明天又陷进去。这块泥地他过不去了。
事完后,他像一头累坏的牲口,喘着粗气,先是那条腿,笨拙的拿过去,有时那东西像在她身上生了根,他拔出时有一种生生的疼。接着他的身体退回去,那只解开她衣服的手,从来不知道把脱了衣服帮她穿上,也不知道摸摸她的腿和胸脯。
男人天蒙蒙亮出去,天黑回来。天天这样,晚饭的炉火熄灭后,家里唯一的油灯亮起。儿女们围着昏黄的灯光吃晚饭,盯着碗里的每一粒粮、每一片菜叶,往嘴里送。正是他们认识粮食的年龄。男人坐在一旁的阴影里,呼噜呼噜把一碗饭吃完,递过空碗,她接住,给他盛上第二碗饭。
她递给她饭时眼睛盯着灯光里的一群儿女,他们一个接一个,从她胸脯上掐断奶,尝到粮食滋味,认出自己喜欢的米和面,青菜和水果。他们的父亲呼噜呼噜把又一碗饭吃完,不管什么饭都吃得滋滋有味。那么多年她只记住他吃饭的声音,甚至没有来得及看清他的脸和眼睛。
四十岁以后的她,那个男人再没看见。她睁开眼睛,身子上面是熏黑的屋顶。她的男人不见了。她带着五个孩子,自己往五十岁走。往五十五岁走。孩子一个个长大成家后,她独自往六十岁走。
现在,她已经七十三岁。走到跟多年前一样的一个夜晚。风声依旧在外面呼喊。风声把一个人的全部声音送回来。把别的人引开,引到一条一条远离村庄的路上。她最后的盛开没有人看见。那个生命开花的夜晚,一个女人的全部岁月散开,她浑身的气血散开,筋骨散开,毛孔和皮肤散开。呼吸散开。曈孔的目光散开。向四面八方。她散开的目光穿过大地上一座座没有月光的村庄,所有的道路照亮。所有屋顶和墙现出光芒。土的光芒。木头和落叶的光芒。一个人的全部生命,一年不缺的,回到故乡。
二、冯三
人的名字是一块生铁,别人叫一声,就会擦亮一次。一个名字若两三天没人叫,名字上会落一层土。若两三年没人叫,这个名字就算被埋掉了。上面的土有一铁锨厚。这样的名字已经很难被叫出来,名字和属于他的人有了距离。名字早寂寞的睡着了。或朽掉了。名字下的人还在瞎忙碌,早出晚归,做着莫名的事。
冯三的名字被人忘记五十年了。人们扔下他的真名不叫,都叫他冯三。
冯三一出世,父亲冯七就给他起了大名:冯得财。等冯三长到十五岁,父亲冯七把村里的亲朋好友召集来,罢了两桌酒席。
冯七说,我的儿子已经长成大人,我给起了大名,求你们别再叫他的小名了。我知道我起多大的名字也没用。只要你们不叫,他就永远没有大名。当初我父亲冯五给我起的名字多好:冯富贵。可是,你们硬是一声不叫。我现在都六十岁了,还被你们叫小名。我这辈子就不指望听到别人叫一声我的大名了。我的两个大儿子,你们叫他们冯大、冯二,叫就叫去吧,我知道你们改不了口了。可是我的三儿子,就求你们饶了他吧。你们这些当爷爷奶奶、叔叔大妈、哥哥姐姐的,只有稍稍改个口,我的三儿子就能大大方方做人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改口,都说叫习惯了,改不了了。或者当着冯七的面满口答应,背后还是冯三冯三的叫个不停。
冯三一直在心中默念着自己的大名。他像珍藏一件宝贝一样珍藏着这个名字。
自从父亲冯七罢了酒席后,冯三坚决再不认这个小名,别人叫冯三他硬不答应。冯三两个字飘进耳朵时,他的大名会一蹦子跳起来,把它打出去。后来冯三接连不断灌进耳朵,他从村子一头走到另一头,见了人就张着嘴笑,希望能听见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可是,没有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冯三就这样蛮横地踩在他的大名上面,堂而皇之地成了他的名字。已经五十年了,冯三仍觉得别人叫他的名字不是自己的。夜深人静时,冯三会悄悄地望一眼像几根枯柴一样朽掉的那三个字。有时四下无人,冯三会突然张口,叫出自己的大名。很久,没有人答应。冯得财就像早已陌生的一个人,五十年前就已离开村子,越走越远,跟他,跟这个村庄,都彻底的没关系了。
为啥村里人都不叫你的大名冯得财。一句都不叫。王五爷说,因为一个村庄的财是有限的,你得多了别人就少得,你全得了别人就没了。当年你爷爷给你父亲起名冯富贵时,我们就知道,你们冯家太想出人头地了。谁不想富贵呀。可是村子就这么大,财富就这么多,你们家富贵了别人家就得贫穷。所以我们谁也不叫他的大名,一口冯七把他叫到老。可他还不甘心,又希望你长大得财。你想想,我们能叫你得财吗。你看刘榆木,谁叫过他的小名。他的名字不惹人。一个榆木疙瘩,谁都不眼馋。还有王木叉,为啥人家不叫王铁叉,木叉柔和,不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