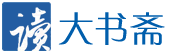匆匆赶去四老太爷宅邸,却见五老太爷及廷狄夫妇俩已坐屋中,正和神色茫然四老太太说话,“四嫂别急,且把心放宽,我们都这般岁数了,生死有命……”
顾廷烨携明兰上前见礼,并为迟来道罪,五老太爷缓缓摆手,神态慈和:“我们住近,自是来些,你们也算早了。……先进去见你四叔罢。”
煊大太太引他们进里屋去,顾廷荧另几个丫鬟婆子正床边服侍汤药,见明兰和廷烨来了,便微微侧身而站。不住唉声叹气:“…大夫说了,一性一命是无碍,但却风瘫了,如今非但不能动弹,连话也不得说了…”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
明兰探头去看,见四老太爷直一挺一挺躺床上,双目半开半闭,仿佛既睁不开也闭不上,四肢僵硬,面部扭曲,嘴角歪斜成一个奇怪角度,喂进去一勺汤药,倒要漏出一半来。
这种情形,也没什么好说,明兰说了几句‘四叔父你好好养病’之类废话,顾廷烨面无表情也意思了两个同义句,然后二人便与煊大太太退了出来。
中厅坐定了,众人开始叙话。
顾廷烨先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好,怎么说倒下就倒下了?”
很简单问题,廷煊却支支吾吾了半天:“…是今儿下午来了封信,说…说二弟西北,又出漏子了……,爹一听,就急得病倒了。”
明兰转头去看煊大太太:“年后大一嫂子不是才说炳兄弟出了些小纰漏么?这是同一回事么?莫非那儿衙门还不肯罢休。”
煊大太太连连苦笑:“是两回事。原先那桩,已差不多打点好了,谁知二弟也太不消停了,身上还没干净呢,又惹是非。说是夜里与人争闹,将人打死了了,二弟也叫打断了一条腿!旧账未清,账又来,打死那人还是良籍,统领恼了,说是这辈子不叫二弟回来!”
明兰默默转回头来。这时炳二太太开始从低音一抽一噎到高音,冲着五老太爷哭哭啼啼道:“我早就说过,西北地方荒芜凶险,人也大多凶恶,您侄儿老实巴交,若非被欺负狠了,怎会与人争执……”
她话还没说完,顾廷烨便打断道:“炳二哥是住流放所里,因使了银子人脉打点,日常连劳作也不用,衣食等均有小厮仆役打点。便是白日闲了,出去逛逛,夜里也该回去了,怎会夜里打死了人?!”
这情由一点明,五老太爷刚刚张开嘴又合上了,摇头捋须。炳二太太难以辩驳,讪讪道:“许是有什么要事,非得出去……”
四老太太忽然冷冷哼了一声:“他是去流放,能有什么要事?家里人为他提心吊胆,他倒好,只知胡闹,还连累了他爹!”越想越火大,好容易给女儿说了门颇不错亲事,眼看议论差不多了,倘若这时老爹挂了,廷荧便得守孝三年,那岂不等成了个老姑一娘一?且别说对方肯不肯等,就算肯等,大约等女儿嫁过去,恐怕什么庶长子庶长女都已生下了。
她素来温文无争,但这会儿捏死顾廷炳心都有了。
一个孝字压下来,炳二太太急了,冲口道:“这也不能全怪他呀,这阵子爹身一子原本就不好,都怪纳那个……”
顾廷煊大声咳嗽起来,脸色涨红,炳二太太才惊觉自己说错了话,赶紧闭嘴。
“说也是。”顾廷烨缓缓道,“适才我也觉着奇怪,四叔父素来身一子硬朗,炳二哥这事也非立即致死,缘何会重病至此?”
这话一问出来,四房众人俱是垂首。四老太太是疲惫中带着灰心,廷煊夫妇却是羞愧兼尴尬,缩坐一旁炳二太太不住骨碌着眼珠。
良久,五老太爷抚须道:“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今儿都是自家人,没什么不可说。”叹气继续道,“当初大哥大一嫂,四哥还能约束一二,自分家后,日益胡闹。近日四哥竟纳了个扬州瘦马,终日嬉乐,大侄子忧心,曾央我来劝,奈何四哥不听,才致如此。”
这话说隐晦,但屋内何人听不懂。
明兰低下头,自行翻译成吐槽版:一把年纪人了,还自觉金一枪一不倒,日夜法克,若只找家里婢女也就算了,毕竟是良家,花样有限,谁知弄来了个职业人士,搞不好还得用了药——连续奋战好些天,已淘澄空了身一子,昨夜兴许刚奋战了三百回合,中午又加时赛,然后下午就听见心一爱一儿子噩耗,当然就抵不住了。
顾廷煊也许还想替老爹遮掩一下,但煊大太太一点护着这老不休公爹意思都没有。
五老太爷转向他们夫妻,慈和劝慰:“四哥糊涂,你们做儿女,又能如何?不顺着他,还得算你们忤逆。大侄子大侄媳,大伙都是明眼人,不会怪你们。”
顾廷煊垂泪道:“多谢五叔父体恤,我,我…我们也是无计可施了…”
“生死有命,到了我们这个岁数,阎王早就惦记上了。”五老太爷微笑道,“大夫既说一性一命暂时无忧,便好好将养着,慢慢也就回过来了。”
这话说温和豁达,淡冲清明,明兰终于忍不住去看了五老太爷一眼。
不过数月未见,五老太爷便如换了个人般,往日那清高倨傲之态全不复见,虽是苍老依旧,却一精一神甚好,说话和气诚恳,十分通情达理。
顾廷烨似也有些疑惑,侧侧瞥了明兰一眼,又附和道:“五叔父说有理,只要有救,好好将养便是。”然后又转头道,“若是缺什么,大哥大一嫂管来说便是。”
煊大太太拭泪而笑:“这里先谢过二兄弟了。”另一边顾廷狄见状,也站起来道:“倘若有用得着地方,也请嫂子哥哥千万别气。”
廷煊夫妇又是感动又是一番道谢。
炳二太太见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仿佛把廷炳事给忘了,大为着急,眼珠一转,低声对身旁丫鬟吩咐了几句,那丫鬟随即点头离去。
顾廷烨转回头来,对五老太爷微笑道:“多日不见叔父,见叔父气色风采俱胜往昔,小侄不胜欣喜。”明兰暗切一声——你不就想问‘老叔,您咋忽然转型了’。
五老太爷笑道:“你不问,我也要说。”顿了顿,叹道,“自那孽障去了后,我夙夜深思,惘然惊觉这一生碌碌无为,竟是虚度了。学问不成,仕途不济,家业不兴,便是几个孩儿也不曾教养好。唉,白活了,白活了……”
顾廷烨默然,私底下他不知多少次嘲讽过这位以文士自叔父,大约也是这个意思,没想到临老了,这位叔父终自己想明白了。
“叔父别这么说……”顾廷煊插嘴,忽又停住,大约想说‘您比我那老不正经爹强多了’,中途刹车。
五老太爷浑不意众人反应,豁达摇摇头:“我已打定主意。再过几个月,待天气凉了,廷狄两口京城看家,我和你们五婶领着循哥儿母子俩,到定州去。”
此言一出,厅中众人皆讶然。
煊大太太是急一性一子,率先道:“定州?那可不近呀。叔父去那儿做甚呀。”
顾廷煊一头雾水,完全摸不着头脑,顾廷烨沉思不语,明兰略略一想,轻声道:“久闻定州山清水秀,文风素着,其中摩尼山院,是天下驰名。莫非叔父……”
庄先生当年就那里深造过。
五老太爷点点头,笑道:“亲家翁比我强得多,不但儿子们各个成器,闺女也教养得有见识。”笑完道,“我昔日有一同窗,现摩尼山院为教席,我欲去投他,这点子学问,教不出举人进士来,可与童子启蒙还是成,也好为循哥儿寻一名师。两相得宜。”
“可,可叔父年事已高……”顾廷煊讷讷道,始终沉默顾廷狄也开口道,“堂兄说是,父亲,三思呀。”
“不必多说了。”五老太爷边笑边摆手,“我这辈子,一事无成。倘若如今再不做,才真是蹉跎一生。”
这事来突然,众人无语,反倒五老太爷心绪十分高昂,说说笑笑,仿佛年轻了十岁。
正此刻,忽然一声凄惨哭叫传来,却见刘姨一娘一披头散发倚门口,满脸涕泪:“求各位叔伯兄弟,救救我家炳儿罢!”说着就跪地上。
刘姨一娘一老态毕露,却也顾不得了:“我知炳儿惹出祸事,好歹看同出一宗份上,莫要不管他呀!”
兀然被打断,众人一愣,五老太爷见不惯刘姨一娘一,皱了皱眉:“休作这番丑态,赶紧起来,廷炳到底是顾家子,我等自会奔走。可他这般冥顽不灵,也该吃些苦头了!”
刘姨一娘一冲着顾廷烨连连磕头:“炳儿以前不懂事,得罪了侯爷,求侯爷大人有大量,饶了他罢,瞧过世老侯爷份上,好歹救他一救。”
——干嘛要看老侯爷份上,难道顾廷炳是顾偃开生?明兰几乎要笑出来。
这话说不伦不类,来来回回这么些陈腔滥调,众人也听烦了,煊大太太正要叫人将刘姨一娘一拖走,却听顾廷烨冷冷开口:“五叔父房里,什么时候有奴婢说话份了?”
刘姨一娘一自进门起,因为四老太爷宠一爱一,满府人对她都是气气,连填房进来四老太太也吃过她苦头,还从未这般被人说过,顿时愣地上。
“炳兄弟如何,自有五叔父和我等兄弟拿主意,与你有什么相干?仗着四叔父心慈,然敢来这里放肆。”顾廷烨目光冷淡,不落痕迹扫了四老太太一眼。
刘姨一娘一被气摇摇欲坠,却不肯罢休,当即把腿一盘,竟坐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虽是下贱人,好歹这房里熬了三十年了,也为顾家开枝散叶,如今老太爷还没咽气呢,就有人这么来糟践我呀!我不活了,我不活啦……”
煊大太太见太不像话了,叫人赶紧把刘姨一娘一捉出去。
这时四老太太忽然站起来,冷声讥讽道:“生出这等上违国法,下忤父兄不孝子,还不如不生呢?那孽障给家里惹出祸事不断,怎么,如今咱们还得谢你刘姨一娘一功劳了?!你再敢放肆一声,我就请侯爷将他逐出宗祠,一了百了。”
众人皆惊,不想素来温和四老太太竟会如此;不过效果倒好,刘姨一娘一立刻不敢哭闹了,瘫地上瑟瑟发一抖。
炳二太太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冲煊大太太哭道:“你们这是要一逼一死我们呀,莫非看着廷炳死外头,等老爷子一咽气,你们就好随意摆一弄了我们了不成?!”
这时顾廷烨忽然道:“炳兄弟之事,我会去奔走。”
炳二太太连眼泪也顾不得擦,喜道:“当真。”
“可丑话说前头。炳兄弟是戴罪之身,又打死了良民,纵是天大面子,十几年是跑不了。嫂子和刘姨一娘一再想轻,就另请高明罢。”顾廷烨悠悠道,“可炳兄弟一再闯祸,便是天王老子也没法子。我想不若叫人去西北,就近陪伴,一来照顾,二来可以提点。”
众人听顾廷烨肯帮忙,有人惊有人喜,又听至少要十几年,要人过去陪伴,便缓缓都将目光投刘姨一娘一和炳二太太身上,直瞧得她们俩心头发一毛一。
炳二太太适才气焰不知哪去了,瑟缩道:“都说长兄如父,廷炳听大哥,不若大哥去。”
煊大太太险些气笑了,上前一步道:“弟妹把肚肠捋捋清楚再说话!如今家里老老,病病,剩下都是女眷孩儿,倘若连廷煊也去西北了,这家谁来撑?所谓夫妻一体,反正父母有我们伺候,弟妹这就收拾收拾,去西北陪二弟罢!”
炳二太太连连摆手,吓得脸色都发白了:“孩儿还小,西北穷山恶水,哪能过日子,也请不到好先生,耽误了功课。”
“百善孝为先!”四老太太满面鄙夷,骂道,“人家一品二品大官,为着守孝,连官儿都不做了。到底功名要紧还是孝道要紧?哼,就是你这种不知礼数一娘一,好好孩儿都教坏了!”她目光转至刘姨一娘一,“既然如此,母子连心,不如请刘姨一娘一过去?”
刘姨一娘一倒有几分胆色,一咬牙道:“成!我们去,我们带着孩儿一道去,但此去不知何时能回,不如先行分家?”四房银钱生意原本都握顾廷炳手中,自他被流放后,这两年廷煊夫妇几乎已都接手过去,趁现自己还清楚底细,赶紧分了家,免得以后两眼一抹黑。
“放肆!”四老太太今日威猛异常,似乎着意要打压她们,骂道,“老爷子还好端端,竟敢提什么分家,你咒老爷子死么?!”
五老太爷也骂道:“你这贱婢,分家这种大事什么时候轮到你置喙?!三年之内分家两次,你想叫人家戳顾家脊梁么!”
四老太太又道:“待老爷子百年之后,想分家也成。要么廷炳回来,要么德哥儿顾廷炳长子及冠,我就做主分家!否则……”她冷冷一笑,刺骨鄙视目光扫过炳二太太,“孩儿还小,不能自己做主。有个不肯陪夫婿吃苦一娘一,一分了家产,还不知会如何呢?”
这话十分难听,只差没指着对方鼻子骂‘水一性一’了,炳二太太立刻哭了起来。四老太太冷冷看着她,也不把话说透,等着以后慢慢当话一柄一。
顾廷煊厚道,似有些不忍,正想去说两句,却被煊大太太扯了下袖子,以目光制止。炳二太太犹自哭哭啼啼,不知如何是好,刘姨一娘一跪地上,看着这满屋人,却渐渐明白了——四老太爷这一病倒,自己祖孙几个,却是要受人拿捏了。
威风妾室做了大半辈子,竟到老了要受罪,刘姨一娘一心里一片茫然。
……
明兰默默看完这一幕戏,一言不发跟着顾廷烨回了府,此时已是灯上月梢,两人各自衣,沐浴盥洗,然后屏退众人,关上房门。
床头雕花四方小翘几本是墨色,可昏黄烛火下,隐隐透出一抹暗一红来,几上放着一把白瓷染青花小矮壶,一精一致壶嘴微微翘一起,烛火轻轻一晃,几面上留下高低起伏一阴一影。明兰裹一着薄缎中衣坐床沿,静静看了好一会儿,方才抬起头来。
顾廷烨躺坐床头,月白绫缎宽袍松松铺床沿,漆黑散发长长垂至□胸前,今夜他没有拿本做幌子,就这么直白盯着她,看她满心疑惑,欲言又止。若是平常,他早主动替她解惑了,可今天……他要看看,她究竟会不会问。
男人嘴角露出一抹微不可查讥意,近乎自嘲。
他就这么静静看着她,看着她挣扎问与不问之间,等着。
“余…余嫣红…”明兰竟觉呼吸困难,对面黑影憧憧帐幕下,男人幽深眸子仿若锁链缠着自己,“……是顾廷炳?”
可怕漫长沉默。
男人收起闲散,声音冷硬如冰岩:“至少三十年,他别想回来了。”
明兰脑中一片空白,结巴道:“可……这是为何?”她设想过很多人,总觉得应是个风花雪月,色胆包天人,却没曾想是整日钻营于权势钱财中顾廷炳?!
“为了银子。”顾廷烨异常平静。
明兰心沉了下去,真想竟然远比预料还要丑陋,起因甚至连逢场作戏都不是。
“余家陪嫁丰厚,除却田庄铺子,嫣红手中至少有两万两现银。嫣红死后,退还余家嫁妆时,这笔银子不见踪影。自然,以当时情形,余家也不会追问。”
“……顾廷炳早垂涎嫣红嫁妆,奈何没有名目,待我出走后,人人都说我不会回来,他便动了心思。”
“可惜东窗事发太早,他只吞没了现银,那些铺子田庄还没法动……”
平静叙述语调,仿若一出残忍闹剧。
明兰胸口压抑难受,“这件事,四老太爷……知道么?刘姨一娘一呢。”
顾廷烨缓缓道:“起初便是他们母子谋划。待第一笔银子弄到后,老子也知道了。”
“四叔父没有制止?”明兰气愤难言。
顾廷烨没有回答,只嘲讽笑了笑。
一个念头脑中一闪而过,明兰冲口问道:“四叔父病可与你有关?”
“有关。也无关。”男人似笑非笑,“我叫人去给那群狐朋狗友传话,我和四叔虽分了家,但还是一家人,可不许怠慢了我家长辈。”
过了半响,明兰又问:“四婶婶……为什么肯帮你?”
“她不是帮我,是帮她自己,帮她女儿。”
“廷荧妹妹亲事……?!”明兰惊觉。
“那门亲事,是我去请托。”
看明兰一脸惊愕担忧,男人笑了笑,“放心,是户好人家,说起来,以分家之后四房情形,还是廷荧高攀了。”
——那么,今日四老太太反常举动有解释了。
“既然妹妹出嫁即,你还,你还……四叔……”明兰急说不下去。
顾廷烨微微皱眉:“这倒始料未及,四叔也荒唐得太过了,亏得没出人命。”
一开始计划,是待廷荧出嫁后,四老太爷才日积月累‘病’倒,谁知那老色鬼猴急太过,提早除了状况,估计四老太太被吓不轻。
“待妹妹出嫁后,想来四婶婶有功夫好好‘照料’四叔。”男人兴味盎然微笑起来。
明兰知道,就像那些风瘫十几年病患,四老太爷大约永远也好不了了,直到去世。
从今日来看,廷煊夫妇起先是不知情,但随着事态发展,煊大太太显然很意识到了问题关键:一旦四老太爷不能动弹,四房大长辈就四老太太,廷煊夫妇倘若想完全压制住廷炳那一房,就必须联合四老太太。
父亲多年老姨一娘一,做儿子不好处置,但正房太太却是可以动手;庶弟远西北,兄嫂总要体恤孤苦弟妹及其孩儿,但四老太太却可以祖辈身份教训之。而同样,没有儿子四老太太,以及出嫁廷荧,也需要廷煊夫妇来撑腰。
正是互利共赢。
到时候,四老太太想怎么‘照顾’四老太爷就怎么照顾,而经过今日,她甚至还有了管束廷炳媳妇把一柄一——只要她一不老实,就让她去西北陪丈夫去;至于刘姨一娘一……儿子不,男人瘫了,四老太太可以出气了。
明兰心头一阵害怕:“西北那边,不会出事罢。倘若叫人知道是你……”
“你以为我做了什么?”顾廷烨哈哈大笑。
“顾廷炳流放西北时,他大哥给带了四个仆役两个婆子,我又给补了两个护卫。这些日子,我时常叫人去叮嘱那些仆役婆子好好服侍,千万要听主子话,不许怠慢违逆,一定叫主子过舒服了,回来重重有赏。又吩咐那两个护卫,西北民风彪悍,定要好好护卫主子,不许叫人伤了去。如此而已。”
明兰呆呆看了顾廷烨好一会儿。
对,他确什么都没做;他只是顺着每个人一性一子,缓慢拉好蜘蛛网。
四老太爷贪花好色,荒唐昏聩,整日厮混也是这么一帮人,顾廷烨传了话后,人家为着巴结顾侯,自然把好货色拿来招待四老太爷——可是,那句传话有什么问题吗。
四老太太一旦入了戏,就只能照着顾廷烨意思做下去,她什么也不能说——不过是做堂兄关心妹一子,替妹一子寻了门亲事而已,旁什么也没有。
至于顾廷炳,顾廷烨太了解他了;他是那种酒色财气,得寸进尺贪婪小人,一旦生命没了危险,又有一众人好吃好喝伺候着,难道他会每日老老实实待流放所里?
不,他必然是耐不住。以顾廷炳之前京城行径——霸占人家祖产,贪图人家买卖,一逼一死人命,难道他西北就会安分守己吗?秉一性一难移,兼之有两个了得护卫,只有他打人,没有人打他,他不横着走才怪。
蜘蛛网拉好了,顾廷烨只需说些似是而非话,然后耐心等待,便会有满意结果出现。
“当初我潦倒,他们不顾骨肉血亲,肆意侮辱欺凌于我,那么,今日就该受了这报应。”顾廷烨一阴一沉了神色,掩饰不住眼中戾气。
杀人不过头点地,这是奇耻大辱,又是受亲人背叛,当时他该是怎样一种屈辱悲愤心情。
想到面前男人然能隐忍至此,明明知道四房父子对自己做事,可这两三年间,他竟不露半分声色,暗中布置筹划——明兰背心发冷,环抱着被子,颤声道:“我我,我没有,从来没有……”她下巴被捏住了。
顾廷烨俯身捧着她脸,笼出一片一阴一影她脸上。
“你嫁给我后,一直待我很好,体贴周全,聪明伶俐。该你做事,你做滴水不漏,不该你问,或是你觉着会叫我不痛,你一句都不会问。”
一阴一暗中,他眉角棱骨愈发显得凌厉森然,不知为何,明兰莫名害怕。
“不论你面前有多少难题,你只自己揣度,有多少疑惑,你都死死忍着,从不主动提起。嫣红事,你心里藏多久了?嗯……说呀,你生一团一哥儿那日,那般凶险,可醒来后,你依旧不曾问起半句……你是怕我难堪吧。可我心中,有什么是比你和一团一哥儿要紧。区区难堪算什么?”
男人越来越重喘气,似是渐渐无法抑制怒气。
“这几年来,你想做事,你想知道,哪一桩哪一样,我没有依你?可你就是不放心,防着我,戒备着我,暗中揣测我,一言一行半点错处都不肯落下!好好好,我果然讨了个好媳妇!”重重一拳击床上,明兰顿觉天摇地晃,眼角淌出一片湿一热。
见她泪流满面,目露惊吓,顾廷烨方才渐渐安静下来,抹掉她泪水,把她连人带被子抱怀里,搂得死紧死紧。
明兰侧头轻抬,这个角度,只能看见他微微鼓起侧腮,紧紧绷着,咬牙切齿般。
作者有话要说:
先跟大家请个假哦,明天晚上有饭局,可能来不及了,就算,字也不会多。
-----------------------------------------------------------------------------
谢谢大家药方,某关十分感动呢,皮肤已经好很多了,感觉皮肤伤害还是中药比较靠谱。
讨论区回复很热闹,我看是看了,实没有时间回复,抱歉了,大家自己聊天吧,等我有时间再来加入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