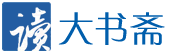第40章
又又和寸寸过周岁,因为满月时没有大办,这次总算给我捞着个机会,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大办了一场,总算弥补了心中的空白。
安朝因为美丽的女儿在人前展示,大受恭维,争足了脸,生日礼物也匠心独运,让人打造了两个金锁,亲自刻上女儿的名字,又刻了祝福语,挂到女儿脖子上,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当着内外臣工,毫不犹豫地说了句:“女儿们,这从今往后,朕有求必应!”
回去后,我笑问:“大言不惭,要你的向上人头,也给她们不成?”
“那又何难,给就是了。”
我冲着他的背影撇嘴,死鸭子嘴硬。
这些礼物,最贵重的是简辽送的两百颗夜明珠,每个都有龙眼那么大,光润无比,说是给公主照屋子,蜡烛烟大。为此我兴奋不已,早想这么办,偏偏安朝亮的是仁政招牌,不好奢一靡一的,反正白送的东西,正好物尽其用。简辽不愧是老相识,怎么就这么了解我的心思呢?我偷笑。
其他的礼物也就是些金银玩器之类,没什么新意,再再给妹妹打了两只野兔玩儿,被我嘲笑是无本的买卖,鄙视了一番。辰儿送的是巴掌大的两只水晶小羊,玲珑剔透,山泉般毫无杂质。妹妹属羊,送这个既有趣,又不失贵重,可见辰儿费了番心思,我也着实感动欣慰。
也许是女孩儿不像再再那样有威胁吧,辰儿也一向喜欢襁褓中的小小的妹妹。利益冲突,再怎么亲,也六亲不认了,都是没办法的事。
“过来,跟你商量个事儿。”安朝对发呆中的我招手。
“咱俩还有悄悄话这一说吗?”我坐在窗下的软椅上,不愿挪窝。
他顿时拉下脸:“你过不过来?”
“过去怎样,不过去又怎样。”我懒懒地瞥他一眼。
“不过来,胗就……”他狠狠地盯着我,然后泄气:“朕就过去。”说着,就要起身。我忙道:“岂敢岂敢。”点头哈腰地跑过去,躬身:“圣上有什么吩咐。”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一眼,沉默一会儿,再看一眼,方道:“这个……还真不好说出口,你也挺喜欢的,想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再说又是别人送你的。”
我在脑中迅速搜索一遍:“先不说什么东西。你想干什么?”
“只是个建议,你不同意就算了。”他清了清嗓子,道:“老婆,你不觉得夜明珠照明太夸张了吗?”
我断然道:“不觉得!”
“小孩子家家的,用这么好的东西,也不合适,你不是说取个贱名长命白岁?咱们不能太溺一爱一她们。”
“这不算溺一爱一。”我急了:“那凌帝当初也是把夜明珠当蜡烛用!”
他当即冷下脸,眼角眉梢仿佛挂满冰柱,沉声:“凌帝有本事,朕没有,你也别跟着朕了。”
我自悔失言,低头:“我不是那个意思……珠子挺好的,干嘛不能用。你是不是有别的用途?”
他看向别处,摇头道:“退回去。”
“为什么?”我愕然:“礼是重了点儿,可简辽也不是外人啊。”
“你知道什么。”他轻蔑地。
我明知无望,一胡一 搅蛮缠:“那你当初干嘛要,现在又要退。”
“我还没说话,你就笑得什么似的,一个劲夸人家碰到你的心坎上了,好意思的。”他叹气。
“那你也能私底下拉我一下,我不就收敛了?”
“你笑得那个样,自从我得了这病,就没见你那么笑过……不是一时不忍嘛。”他沉痛地:“败就败在个不忍上。”
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又被触一动了,酥一酥的,麻麻的,比做一爱一还舒服。我凝视他,柔声:“想退就退吧,我都听你的。”
“呃?”他讶然,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缴械。
我嫣然一笑:“你说怎样就怎样。”
“老婆……”他回过头,感动地握着我的手,无语凝噎。
真希望一生就这么过去,暖暖的,柔柔的,恬静一温一 和,像冬日一温一 泉。安朝不是十全十美的好男人,我也不是完美的女人,我们的生活磕磕绊绊,可真希望就这样,一直这样,直到老死。
“简辽得罪你了?”
“知道了又帮不了什么忙,白费我吐沫。”他的讨厌劲又上来了。
我“切”了一声:“谁稀罕知道啊。”
他看着我,又去看墙上悬的天地宝剑,缓缓道:“有人参简辽谋反。”
我想也不想就喷笑了:“你信吗?”
“我信不信,和这事本身无关。”他的目光四处游一移,就是不落到实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沉思片刻,冷笑:“刘邦想杀功高盖主的韩信,明明有的是机会,最后却没杀成。一起打下一江一 山的情义,不是轻易就能抹杀的。若无韩信,刘邦不一定能夺天下,若无简辽的兵马相助,你也不会这么容易做上皇帝。不说滴水之恩涌一泉相报,也不好忘恩负义,过桥一抽一板吧?我不懂政治,也搞不清什么叫合纵连环,相互利用,但有一点,即使没有法律约束,有些人也遵守自我准则,这叫道德。”
他并不看我,仿佛我刚才没有说话,望着随风轻摆的帐幔,取下扳指握在手里,有一下没一下的翻转着。
“的确是没有独占鳌头,只有日月轮转。”我微微苦笑:“安朝,你打定了主意,谁也左右不了,我只有一句,今日是刀俎,未必永远是刀俎,风水轮流转,人无定数,乃是天意,既然如此,何必为难身边的人。简辽没有谋反,没有就是没有,兄弟就是兄弟。”
“你说的是这件事吗?”他侧目。
安都和安建,一个被他毒死,一个被他借刀杀人,反正都给弄死了,这是前不久的事,他的怀疑,原也有理:“我没有隐射你的意思,随你怎么想罢。”
“你当我真的容不下简辽?”他猛然坐直,又颓然软倒,重重靠向椅背:“我是为咱们的儿子铺路!”
我缓慢而坚定地道:“再再不需要这条路,即使你铺得再平,我的儿子也不会走这条路。”
“辰儿呢?辰儿也不需要?”他道:“你不愿再再做储君,那走这条路的,就是辰儿,如果你认为辰儿不需要,我们立即停止讨论这种问题。”
我不愿再再为保地位,和他哥哥争得你死我活,重蹈他爹的覆辙,可也不希望辰儿是个彻头彻尾的安朝。我一爱一这个男人不假,可并不欣赏他的处世:“简辽反了吗?如果你把所有不是危机的东西都看成危机,那么天下就没一个可信之人。仅仅因为位高权重就列入清理名单,我只能说你太可怕,你的行为对于掌权之人来说,是正确的,可你只是正确,除了这个,一无所有。”
“你以为皇帝有什么,不都是除了皇权一无所有。”他淡淡地。
“你嫌我哆嗦,无聊,无聊到无一耻,是不是?”我得出去逛逛,再看着他这副嘴脸,我会疯掉:“简辽帮过我们太多,也帮过我的孩子太多,没有他,我的孩子到现在还是一文不名的野孩子。我们这一家人,朝不保夕,今晚睡下,不知道能否看到明天的太一阳一,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也许你愿意忘记,因为你是已是皇帝,可我不会忘,我更加不会忘记,身在良州的那段日子,孤苦寒微,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他动了动嘴,我不等他说话,转身而去。听他狡辩已成为一种酷刑。
是不是所有功臣良将的结果都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那些当初的誓言,一句身不由己便可忘记,同生共死,成了你死我活,是不是所有坚固的东西,最后的结果都是破碎?或许我太天真太愚蠢,做不了杀戮决断之人,只配做被人决断的蝼蚁。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所谓无奈,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