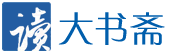出城时并没费太大的事,守门的小卒见车一内一就一半死不活躺着不动的孕妇,二话没说就挥手放行了。w
我从未赶过马车,也从不知道这看似轻松的活其实一点都不轻松。在城一内一街道笔直顺坦,我还容易掌控些,可到了荒郊野外,那马就开始不听使唤了。我不一抽一鞭子,它自顾自的溜达到路边啃青草;鞭子一抽一得轻了,它左右前后乱踱步;一抽一得重了,它突然尥起蹶子便狂奔发癫,横一冲一直一撞,大有不把马车掀翻誓不罢休之势。
九月的天气,原该凉爽怡人,可我却被一匹马整得大汗淋一漓。
道路颠簸,我还好些,但邓婵是一足月的待产妇,挺着个大肚子在车子受难的滋味却想来不会好受。出宛城时她还是躺在车里纹丝不动,像是傻了,可没等我把车赶出五里,她就开始哼哼了。
先还很小声,渐渐的呻一吟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让人揪心,我就算想狠心忽略都不成。
“疼啊……”终于,她开始大声嚷叫起来,“疼死我了!我要死了——疼、疼死了——”
我持鞭的手一抖,愈发不知道怎么赶车了。
邓婵的叫一声一声比一声凄厉,眼见得日头一点点的从地平线上往下坠一落,我的心不禁也跟着颤一抖起来:“表姐!你撑着点,算我求你……无论如何请你撑着点!你可别在路上生啊!”
我的哀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甚至连一点微薄的安一抚一性一也不具备,邓婵反而叫得更大声了,不断在车子里打滚似的乱撞东西,我能清晰的听到陶罐碎裂的脆响,能清晰的听到她越来越粗重的喘气声。
“丽华……我不成了……”她憋气,伸手过来拽帘子,“帮帮我!丽华……”
我焦急的扭头,只听“哗啦”一声,偌大一片竹帘子竟被邓婵拽塌,她的手指紧紧的握成拳,竹片的碎屑甚至还插在她的掌心,殷红的鲜血顺着指缝滴滴答答的往下落。
“邓婵?!”我慌了神,顾不得再控马指挥方向,反身爬进车厢。
邓婵面一色一煞白,眼神涣散的望着我,开裂起泡的嘴唇缓慢的一开一合:“我……不生,丽华,帮我……不生……”
她蜷缩的躺在车厢里,空间一逼一仄,她的一腿一无法伸直,弯曲的膝盖在剧烈的颤一抖。我无措的望着她:“我要怎么帮你?邓婵,我要怎么帮你?”
要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六神无主,慌手慌脚的托着她的头用力试着想将她扶起来。
“啊——”她凄厉的惨叫一声,许是牙齿咬到了舌头,雪白的牙齿上沾染殷红的血丝,森冷的咧着,说不尽的恐怖。
她憋住一口气,似乎这口气永远也缓不过来了,膝盖的抖动带动整个身一子剧颤,抖着抖着,最后竟像是肌肉痉一挛般一抽一搐起来。
“邓婵——”
“嗯……”她呻一吟,时而惨叫,时而低喘。迷殇的眼神,濒死的挣扎着,这一幕在我眼前不停的晃动。
我颤巍巍的将她放平,低下头,目光往下移动,只见自己膝盖所跪之处,正在逐渐漫开一汪血海。
血般绝艳的红一色一蜿蜒至车厢的各个角落,我打了激灵,双手扯住邓婵深衣长裾的裾角,用力一撕。可我之前已骇得手脚发软,这一扯竟然没能把裙裾扯裂。
我随即低头,用牙咬住布料的一角,用手借力一扯,只听“兹啦”一声,裾尾终于被我扯裂。
深衣一内一是一条没有缝裆的白一色一长袴,我已经看不出它原有的颜一色一,鲜红的血液将它染成了暗黑一色一。
我从不知道原来生孩子是这么恐怖的一件事,原来一个女人一体一内一居然可以流那么多的血……
“表、表姐……邓婵……”我哽咽的带起哭声。天杀的,这个时候我脑子一一团一糨糊,浑浑噩噩的像是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痛……”邓婵的眼睛闭着,呻一吟的声音也越来越低,“我不要生孩子……”
“邓婵……你撑着点,求求你!你现在不能放弃啊……”
“我根本……嗯——哼。”她一抽一搐得愈来愈厉害,一阵阵的肌肉痉一挛,样子十分骇人,“不……一爱一那个男人,我……为什么要……替……他生……”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声嘶力竭的疯狂呐喊:“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车厢一内一的光线越来越暗,等到天一色一完全暗下,整个天地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再也看不到邓婵的样子,只能听见她断断续续的痛苦辗转、呻一吟:“表……哥……表哥……表哥……”
我泣不成声:“邓婵,你醒醒,求你把孩子生下来……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唉……”她突然幽幽的叹了口气,语音低迷凄婉,透着无限绝望,低不可闻,“你、你……为何从不看我……一眼……”
我哭了许久,她却再无动静,甚至连半丝叹息也吝于再施舍给我。我麻木的跪在温一热的血水里,浑身冰冷。
“邓婵……”颤一抖着双手,我摸上她的身一体,她就这么躺在我面前,面庞冰冷,气息全无。
寂静的夜一色一,浓得像一团一永远也化不开的墨。
我身一子一震,只觉得一胸一口撕心裂肺般的剧痛,呆呆的跪在她面前,捧着她的头痛哭失声。
请记住本站新域名:www.dashuzh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