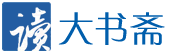孙泰这里急不行,暗里琢磨,怎么他妹一子哪儿也没音儿没信儿了呢,这边范敬隔三差五要银子,他是真有点儿打点不起了。
这日好容易盼着他妹一子给他送了信过来,说让他过去一趟,孙泰急忙就赶了过去,进了她妹一子屋子,就见他妹一子正病歪歪坐炕上,一精一神头都没了。
孙泰忙问:“这是怎么了?才几天不见怎就病了?”孙氏看了他哥一眼,想到这起子事,就觉得心里一阵犯堵。
本来封景山子嗣不旺,大房就得了两个姑一娘一,二房也是一个丫头,就她肚皮争气,生了个小子,虽说后来也有个妾生了小子,可不如她生大少爷聪明,书念也不大好,因此倒是她所出这个儿子得封景山意,加上一娘一家也有钱,虽比不上正经儿大太太,却也颇有体面。
上头大太太二太太便是心有不甘,也没法子,可那日大太太巴巴把她叫了去,问她:“可是撺掇着爷去那府里寻事了?”孙氏一时觉得没什么值得瞒着,便说:“是我一娘一家哥哥打官司,那边后台硬,让爷去那府里垫句话。”
她一说完,大太太就冷笑一声道:“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哪个牌子上人,巴巴赶着去寻不自,你自己找死,没得拉着我们一府人跟着你倒霉,成日就撺掇爷帮你那个一娘一家哥哥,如今外头还都传说,你们家仗势欺人,你仗谁势,你自己心里没个底儿啊!你说你哥哥也不长眼,欺负人也不挑挑,旁人你欺负还罢了,瞎了眼,非跟苏家打官司,你可知苏家是什么人家?”
孙氏诶她说不服气顶了一句道:“不过是个商人罢了,纵他家叔老爷有些体面,也不过一个三品官……”她话没说完,大太太一口唾沫啐到她脸上:“呸!三品官,你可知国公爷都相中了她家二姑一娘一,要给子都说亲事呢,你现还想仗着国公府势去跟人苏家打官司,你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孙氏大惊,哪想到后是这么个结果,被大太太攥着把一柄一,当着那些婆子丫头面,狠狠给了顿没脸,孙氏回来一气,又想惹上苏家这么个来头,他家买卖甭说,也做不下去了,又是一急,便病了。
病了几日也没见封景山过来瞧她,孙氏心越发凉起来,挣扎着起来,让人去给她哥送了信,孙泰一来,孙氏忙着把前因后果说了。
孙泰也吓了一跳道:“不能吧!”他可知道底细,苏家二姑一娘一可不就是那位跟他结了仇二公子吗,两家从冀州打到兖州,如今打到了京城,这个疙瘩早就系死了,那还解一开,那丫头抛头露面做了这些年买卖,难不成,到头来还能嫁进国公府当一品夫人,这怎么可能,就是说书,都说不出这样荒唐故事来。
孙氏道:“这事千真万确,国公爷都相了,听说过些日子过了一娘一娘一眼,就差不离了,是小公爷自己相中人,死乞白赖非得娶,你也知道国公府就这一个嫡子长孙,过了年可都二十五了,好容易他自己有个相中,便是门第上不大般配,国公爷都点头了,旁人自然插不上话,这亲事便□不离十了,如今咱们家非要跟苏家过不去,不就等于跟国公府别着劲儿吗,俗话说好,这腰哪能拧得过大一腿,哥哥,你回去瞧瞧,寻个中人跟苏家说和说和,没准还能有救。”
孙泰回来越想越心惊,跟苏家这官司打下去,他还能好了,可这个中人还真不好找,孙泰想来想去,真就让他想出来一个。
俗话说得好,拔脓还得好膏药,而范敬就是一贴好膏药,自然,这家伙贪,这竹杠让他敲下去,真能伤筋动骨,可伤筋动骨也比关门强,这上百年恒升福要是他手里倒了,将来到了地下,他也没脸见孙家列祖列宗了,留得青山不愁没柴烧,先过了眼前这难关再说。
孙泰琢磨好了,第二日就去了范敬府上,范敬他是见不着,跟钱师爷把事儿一露,钱师爷让他回去听信儿,自己来了后衙跟范敬道:“大人您说这孙泰怎么忽然就要说和了?前两日还非得要把官司打到底儿呢?今儿听他那一话意思,认头掏大银子了事呢,大人你看这儿……”
范敬敲了敲桌子道:“这孙泰老一奸一巨猾,从来就没有认头吃亏时候,这一回这样,定然有个大缘故,明儿他再来,你把他叫到后头来,我见他一见,探探他话儿。”
第二日一见孙泰,范敬就道:“这一阵子,赶上年下,公事繁忙,倒是怠慢孙东家了,莫怪莫怪啊!”
孙泰暗道:你个老狐狸,可面上却忙道:“哪里,哪里,大人给朝廷当官,为百姓做主,辛苦辛苦!”
两人寒暄过后,孙泰直奔主题道:“也不瞒大人,跟苏家这官司,我想着早了早好,大年根下,也别给大人填麻烦,这事说起来,都是我不是,您看看是不是跟苏家那边说说,替一我递个话,我摆下酒,请不到他家二公子,请了王掌柜来,当面说开了这事,不就完了,说白了,都是做买卖,也没啥深仇大恨,我这手里还有两个上好铺面空着,听说竹茗轩正寻地儿,这个就当我赔罪礼了,您看如何?”
范敬一愣,心话儿这孙泰历来不是个大方,哪次不是自己拼命挤,才能挤出几两油来,这回怎这样大方起来,瞧这意思是真怕了苏家,知道自己这官司没赢可能了,也惹不起,才想着破财免灾呢。
孙泰越这样,范敬也开始犯嘀咕了,这苏家后头除了参领大人,可还有什么仗腰子厉害人物不成,自己需打听清楚了,别到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
想到此,范敬咳嗽一声道:“他竹茗轩茶毒死了柳枝汉子,这个官司可还没审明白查清楚呢,孙东家怎就想这么了了。”
孙泰苦笑一声道:“范大人,您别吓小了,小是有眼不识泰山,我这眼睛长脚地板上了,没认出真神来,先别说皇后一娘一娘一这个大姑姐,就凭国公府这门亲事,给我八个脑袋我也惹不起苏家二姑一娘一,她是我姑一奶一奶一,我孙泰服了,心服口服。”
范敬也有些傻:“你说苏家跟国公府有姻亲?我怎么没听说?”孙泰道:“这事如今还没挑明呢,我妹一子跟我说,小公爷瞧上了苏家二姑一娘一,国公爷也相过了,估摸一着迟明年春就下订礼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苏家以后跟皇上都占了亲,我算干啥,敢惹她,不是自己找死吗。”范敬大惊。
采薇这几日正忙,打年根底下,冀州府,兖州府掌柜都来了京里,一个是报账,二一个,也说说这一年经营情况,连着苏府角门处,单辟出一个不小院子来,让采薇使唤,采薇就这里对账算账,见这些掌柜,也顺便把年利分红放下去,让他们赶着回去给伙计们发了,好过个年。
几十个掌柜聚院子里,总也没见面,这儿见了面,倒是有说不完话,吵吵嚷嚷挺热闹。
采薇吃了早上饭才过来,那些掌柜一见她进了院,倒是挺齐整行礼:“给二公子拜早年了。”
采薇倒扑哧一声笑道:“这才几啊!你们这年倒是拜早。”三月道:“算你们几个乖滑,等走时候,每人一份年礼,捎回家去,也算我们公子一点心意了。”
几十个掌柜都知道二公子一向大方,只要规规矩矩把她交代下买卖干好了,二公子真舍得放赏,忙眉开眼笑谢了。
采薇道:“你们先别这会儿谢我,一会儿若是谁账上给我不清楚,可别怪我给他没脸。”说着进了屋去,正中一张花梨罗汉榻,榻几上已堆满了高高一摞账本子。
三月服侍着采薇坐榻上,又把脚炉点了,放她脚底下,屋子四角早点了炭火盆子,虽采薇不喜炭火,可这屋里四敞亮开着,又是大冬底下,也真怕她着了寒,刘氏便不依着她,让下面人早早就把炭炉子备上了,烧了这么大会儿子,屋里倒是熏得分外暖和,外面大一毛一衣裳就有些穿不住。
采薇伸手解了前面系带脱了,里面却只穿着一个紫缎棉袍,三月怕她冷了,又拿了斗篷过来给她搭腿上。
采薇这一忙起来,直到近晌午,才略略抬头,刚抬头,王宝财进来道:“二公子,府衙钱师爷刚头来了,把咱们送去东西都送了回来,连西郊房子地契都没留,还说孙泰送了话来,说想了这官司,问公子可有空闲,孙泰摆了酒,要给公子赔情呢!”
三月声笑道,姑一娘一可真神了,那日送那两个汝窑玩器时候,我还舍不得,好容易淘换来好东西怎么就送人了,您说这好东西不过是出去溜达一圈,早晚还得回来,这才几天,还没捂热乎呢,可不就转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