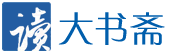又到了大四学生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了。最近,几乎每天都有粉丝问我,咪蒙,到底该做我喜欢的工作,还是世俗意义上的好工作?
对于中国家长来说,世界上唯一的正经工作,大概就是公务员吧。我爸曾经也这么劝我。
当时高考填志愿,我不管报哪个院校,都只填了中文系。一张写满了中文系的志愿表,也是够变一态的。当时最流行的是学经济,而像我这种账都算不清的傻×,学经济纯属自取其辱啊。关键是我不喜欢。从小到大我做任何事,首先考虑的都是我喜不喜欢,而不是有没有用。我爸得知我想考中文系,用一种挽救失足青年的眼神看着我,说:你告诉我,学中文有什么用?
我用一种挽救失足老年的眼神看着他,回:那你告诉我,你成天打麻将赌一博有什么用?
我如愿以偿地念了中文系。
有一天,我一边拉屎一边看报纸。《南方周末》上登了新年致辞: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一阳一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
简直好燃啊。
我眼含热泪从厕所出来,同学问我:怎么了?你屁一股痛啊?得痔疮了?
我说:我要进报社。我要去南方系。
我去了很多家报社实习,在广州《新快报》实习的时候,我和摄影记者去采访收容所,差点儿被打;揭露大学黑幕,采访校长时被他指着鼻子威胁,说我“太年轻,不知道世事险恶”,我照样写了批评报道。实习老师觉得我蛮有做这行的潜质的,把我推荐到《南方都市报》。
在《南方都市报》实习,印象最深刻的是,新闻部副主任王钧让我和她去参加一个政一府会议。那真是一个无聊的会议啊,现场好多记者都睡着了。只有王钧一直在认真听,认真记笔记。只有她抓住了会上一句话带过的信息“广州居民用水价格可能会上调”。她追着有关部门采访了四个多小时,对方从不耐烦到大发飙,觉得《南都》多事。不管怎么样,稿子写成了。第二天,《南都》用头版头条写了水费即将上调的新闻。其他报纸的头条都是站在官方立场发布政一府报告,只有《南都》站在市民这一方。
所谓敬业,就是要以虔诚的姿态对待你手里的每一件“小事儿”。
所谓媒体,就是永远要站在受众的立场。
这两种态度影响了很多年。
这是王钧教会我的。
前年10月,我在微博上看到消息:王钧43岁,得癌症去世。还记得实习的时候,她一直说自己身上好痛,但是没时间去医院。去医院一天,就会错过一条大新闻,她舍不得。
在《南都》12年,我学会了太多。南方系最好的一点,就在于致力于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启蒙。有人说,启蒙是一种出走,是去引领大家看到一种别样的可能一性一。
我写文章、写书,现在写剧本,一直想做的,就是给大家提一供一点儿别的可能一性一,让大家换一种角度,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社会,看待这个世界。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事儿。我从中可以获得价值感。
最近两年,我转行做剧本,坦白说,刚进这行,我也会动摇。
写剧本是我喜欢的事,因为我可以学着用影像的方式,去讲一种新鲜的价值观。但,我真的适合做这行吗?喜欢的事就一定能做好吗?万一我花了很多年,依然写不出一个好剧本,怎么办?
每当我纠结的时候,都是我身边的这帮人,带给我新的力量。
有个二次元迷迷糊糊的妹一子,她叫茜半仙,被父母一逼一去英国学习国际贸易一年。还好,她英文不错,在英国,她灵活使用三个单词:this, this, andthis。
她没有朋友。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日剧、韩剧以及动漫。她想跟人聊《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我不受欢迎,怎么想都是你们的错》《我的脑内选项正在全力妨碍学园恋一爱一喜剧》……别人都觉得她有病。
我看到她在豆瓣的剧评,觉得这妹一子很有才,发豆邮给她:“要不要来我的一团一队实习啊?”她立即辍学回国了。
她说,她终于可以每天只聊电视剧了!终于有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了!我们的剧本写作是一团一队式的,每个人负责自己的角色,为你的角色设计戏剧桥段,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每个角色都能出彩。
她每天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在剧本讨论会上,为了维护自己的角色,跟其他人撕B。她一分钟也不敢缺席,因为只要离开一分钟,其他人就会偷偷给自己的角色加戏,而她的角色可能会受损。她经常憋尿,厕所都舍不得上。而且,没多久,她就成了撒谎一精一。
每次发烧,都装没事儿。我看她脸特别红,问她,你是不是不舒服?她说没事儿啊,我只是有点儿热。我看她都有点儿发一抖了,强迫她回家休息。她说:不行不行,我只是有点儿感冒。我感冒必须传染给别人才能好,所以我不能回家!必须留在公司,才能传染给别人。
还能比这更扯吗?
有一次开剧本讨论会,正说着话呢,茜半仙突然一抽一搐,脸不停地发一抖,牙齿打战,手蜷缩起来,掰都掰不开。大家都吓坏了。我们手忙脚乱地送她去医院,挂急诊。
医生都吓到了,严厉地跟茜半仙说,你这是严重缺钾!再不来医院,你会心跳骤停,猝死!医生还说,你的钾含量太低了,一般人低到这个程度,路都走不动了,你居然还上班!你们什么单位,你们老板是不是人哪?!
其他人转过头看我。
我心虚地说:我们老板不在,他,他确实禽一兽不如。
我吓坏了,骂茜半仙下次生病千万别装没事儿了。
结果,刚打上吊针,她缓过来了,不一抽一搐了,立马来劲了,欢快地说,反正大家都在,不如我们接着开会吧!
我怒了:你娃想当现代焦裕禄啊!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我,你真出了事儿,老子会被判刑的!
她伸出一根手指:那我们只讨论一小会儿?
是不是很变一态?
是的。
其实以前我挺歧视勤奋的。我觉得勤奋的都是傻×。但是,做了这行,遇到这种看起来很逗B,其实很正能量的人,内心真的很受触一动。
当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是忍不住要勤奋的啊。
我要讲的另一个人,叫李野。
他身高一米八六,身材魁梧,长得特凶,一瞪眼大家都害怕。他曾经是混黑社会的,业余一爱一好是写小说。大学毕业,父母强迫他走正道,安排他去银行上班。于是,他被称为服务业的噩梦。他每天走进银行,那眼神,那姿态,不像要去上班,倒像要去打劫。别人来存钱,一看他的样子,钱都不敢取了,只想回家。他连续好几天把顾客吓到。据说他旁边的银行生意越来越好。
经理让他微笑服务,他微笑服务之后,银行就彻底没人了。一个长得凶的人硬要装和善,更可怕啊。那个时候他特别痛苦,当然他的经理更痛苦。他每天都想找时间偷偷写小说,但是没法写啊,经理成天跟盯着贼一样监视着他。
他决定老子不干了。他想当编剧。他给我们一团一队投了简历。
我面试他的时候,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呃,如果不录取你,你会拿一枪一崩了我吗?
他说,不会。
于是我录取了他。
谁敢保证他说的是真话啊。
我们一团一队的一大特质就是欺善怕恶。李野来了之后,大家都很怕他,每次讨论剧本,只要他提任何建议,大家都鼓掌鼓掌,说:好一棒啊好一棒啊!慢慢地,大家发现,他的眼神越来越柔和了,他的语气越来越温柔了。有一天,大家发现,这个一米八六的大汉,居然在看《元气少女缘结神》!
一妈一呀,他根本不可怕好吗?于是剧本讨论会上他再提什么建议,我们只要觉得不好,就会直接说:什么玩意儿!滚!
有一次公司要拍一个短剧的片头,需要有人上身穿西装,下一身穿内一裤,出去跑步……
我说,李野,你来吧。
他愣了下,说:哦,好。
拍摄的时候,一路上都有人盯着他嘲笑。在世界之窗,一个大一妈一看着他的奇装异服,感叹:如今的社会怎么了?
他一扭头,凶狠地一瞪,怎么了?你说怎么了?
我怕他生气去砍人,问他:你没事儿吧。
他温和地笑笑:没事儿。
公司拍短剧,他演秃头、演一娘一炮、演人一妖,啥都演过。
如果剧本写得不好,我想怎么骂就怎么骂。
他还道歉说,对不起。
说好的黑社会呢?说好的逮谁灭谁呢?
他说,以前一直想写小说,想拍电一影,他的梦想是要拍出《低俗小说》《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那种很酷炫的片子。在银行的时候,做着自己觉得很无趣的事,他对世界越来越有敌意,简直有点儿愤世嫉俗了。当他终于可以每天写剧本、做喜欢的事时,他说,自己血液流动的速度都快多了。在这种很燃很热血的状态下,其他事都算个屁。被骂算什么?丢脸算什么?
有时候,为了写好剧本,我也需要去求圈内的大神指点,我也需要低声下气,我也觉得有点儿丢脸。但是,想想李野这个曾经的黑社会,站在街头只穿内一裤的样子,我突然有了丢脸的勇气。
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超级大抠B,他叫许超。他以前是一家杂志社的副主编,听上去很高大上吧,其实本人就是一—一毛一—不—拔—的矮矬穷!
他住在城中村,下班回家,天气超热,同事邀他一起喝糖水。他一看一杯糖水三块钱,这么贵,当场扭头走人。有一次他发烧,烧了三天,舍不得去医院,后来终于好了,大家问怎么好的,他说,老子买了药的!花了两块钱哪!他人生中最奢侈的一次,就是有急事儿,咬牙打一次摩的,花了七块钱巨款。他的头发永远都是自己剪的,我们跟他说街头剪头发很便宜哎,才五块钱。他说,什么?剪次头发五块钱,简直是打劫!
这样一个极一品抠B,有一次公司要拍短剧,需要买一个道具。淘宝上这个道具有两种价位,一种15块,一种750块。公司预算有限,买了15块的,一妈一蛋,太简陋了,我们看了实物,简直丑哭了。怎么办?
许超说,买750块的吧!我来出这个钱。
我们都惊呆了:你疯了吗?
许超很奇怪:怎么了?我只是不想看到自己喜欢的短一片被拍成一坨屎啊。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抠门儿,而是只愿意为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花钱。为了喜欢的事儿,我们可能会突破原则,突破底线。
所谓热一爱一,就是破例啊。
还有个很乖一巧的女孩,叫小颖。她以前做的是最正常的工作。
每天早上乘地铁的时候,地铁上的人都死气沉沉的,好像已经劳累了一整天的感觉。每次她都会问:为什么要每天痛苦地坐地铁,做一天痛苦的工作?她也考虑过梦想这件事儿,觉得“梦想”这个词离自己很遥远,那是有钱孩子才能追寻的吧?但是,她实在受不了公司的氛围,那种每个人都偷工减料、投机取巧的氛围,她每天做的事儿也毫无价值。她跟上司说好了,自己要辞职。上司让她多待一个月,做好交接。
终于熬到辞职前最后一个星期,男朋友很贴心,给她买了一排养乐多,说,一共五个,每天一个,喝完了,你就可以解脱了。她很开心,期待着周五下班那一刻。终于到周五下午,深吸一口气,喝完第五瓶养乐多,结果上司说,拜托你,能不能再多上一天班?她当场就忍不住哭了,为什么五瓶养乐多喝完了,还要再上一天班?她来了我们一团一队,再也不哭了。
她迅速变成每天都想加班的变一态。有一次我让她早点儿回家,不用加班了。第二天,她过来找我:老板,是不是我最近表现不好,不配加班了?她还莫名其妙地成了我的监工。
每一次我想偷懒,都会被她抓到。
她总是恨铁不成钢地训斥我:老板哪,你能不能勤奋点儿?
说好的乖一巧呢?嗯?
跟他们小组开会,都夜里1点了,想到第二天9点还要上班,我就说,要不我们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她瞪了我一眼,说:再讨论一个小时吧。你要着急你先回家呗。
她眼神那么严厉,我哪敢回家啊。
弱弱地问一下,到底谁才是老板哪?
是的,这就是我每天经历的一切。
我们一团一队,因为工作强度太大,有个男生累到连续晕倒两次,还跟我说,挺好的,体验了一下晕倒是什么感觉,下次写剧本写到晕倒戏,就更真实了。
因为担心大家的身一体,我强制一性一地不允许大家周末加班,每周怎么也得休息一天。然后公司阿姨告诉我,又有人周末偷偷来加班了,她把名字都记下来了。
为了节省时间,很多员工都睡在公司里,害得我都不好意思回家了,只好也住在办公室。
以至于我的很多朋友都说:咪蒙,你变了,你以前不是号称要“用生命在鬼混”吗?你娃怎么越来越勤奋、越来越励志了?一奶一奶一的,你以为我想啊?还不是被员工一逼一的。
不是我的一团一队有多好、有多棒,而是因为当你做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会激发出你人一性一中最美好的一面。
你愿意超越功利。
你愿意不计较得失。
你愿意付出一切。
他们不是在扞卫这个公司、这个一团一队,而是在扞卫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不管任何时候问我,做喜欢的工作,还是世俗意义上的好工作?我都会选前者。
做你喜欢的工作,我不能保证你成功,但我能保证你快乐。
这种快乐,来自你全身心投入,每天都在进步的满足感。
有人说,选一个一爱一人,
决定了你每天上一床睡觉前的环境。
选一份事业,
决定了你睁开眼每分每秒的心境。
人生超过1/3的有效时间都会花在工作上,那么,何必要让这1/3的人生都处于痛苦中?做一份所谓的安稳的工作,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来,知道50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做你喜欢的工作,你反而看不到清晰的未来,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你充满了各种可能一性一。
还有什么比活在对未知的期待中更酷的呢?
大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