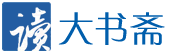夏小末手中的勺子敲在陆荷白的脑袋上发出“咚咚”声响,她尴尬地笑一笑:“陆荷白,你不会当真了吧,我在跟你开玩笑呢。”嘴上虽然那么说,但是夏小末的心中像是打翻了一个五味瓶,如果刚才陆荷白爽一快地答应下来,说不定自己真的就成为他的女朋友了。
抛却莫离在她心中的地位不说,那一刻的她倒是真想把自己托付给眼前这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男孩。
然而,回头想想这种假设又有什么意义呢,完全是人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感情寄托而已。
莫离跟陈柔谦完全淡出夏小末的生活,是在新年过后的第一个月,一个半月的假期夏小末只回家呆了三天,她受不了父亲在一妈一妈一面前低眉顺眼的样子。临行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偷偷地推开了她的房门,默默地帮她整理着行李。
良久,他缓缓地说:“小末,如果有一天爸爸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会原谅爸爸么?”
他的声音异常低沉,问完以后,深深的叹息一声,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借着昏暗的灯光,夏小末悲哀地发现这个不到五十岁男人的头发,大部分已经花白,看着叫人心酸。她说:“爸,您从小对我好我都知道,就算是偶尔做些错事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么?”
夏小末说话的时候,故意笑了笑,周围悲怆的气愤实在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后来夏鸿升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坐在沙发里一抽一了半盒香烟,最后检查了一番女儿的行李,方才开门出去。直到回到学校后的第二天,夏小末收拾东西的时候才发现,爸爸那天帮她检查行李,其实是为了瞒着一妈一妈一偷偷地塞给她一张银行卡。
那银行卡里有多少钱夏小末不知道,但凭直觉一定不少于六位数。
她把银行卡从书包里面掏出来,藏在了床下,她盘算着某一天说不定自己就和莫离破镜重圆了,那时候她可以支援她买一辆四处露风的吉普车。
那天莫离来找夏小末的时候恰巧碰上了陆荷白。
陆荷白是夏小末为了给biubiu洗澡而特意叫来的,这条陆荷白买来的大狗胃口奇好,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已经全面发展成一只水桶,每次给它洗澡都是痛苦的经历,需要另外一个人拿着一块骨头吸引它的注意力。
莫离那一次突然拜访,被陆荷白的严厉抨击了回去。因为他来这里,竟然是要告诉夏小末说陈柔谦要搬到自己那里去住了,问她是不是要把自己的东西搬到这边来。最可气的是,他还为自己这种卑劣行径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陈柔谦之所以搬到他那里住是为了省下一千二百块钱的住宿费给她家老爷子治病。
夏小末哭笑不得,天底下哪有这么混蛋的人,就算是学雷锋做好事也没有这么学得这么彻底的吧?她冷笑一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那些东西我不要了,老一娘一嫌脏。既然想省钱看病,为什么不连学也一起休了啊,那样岂不是省下更多?”
biubiu已经学会了夏小末察言观色的本事,它像一一柄一利箭似的冲向了莫离。陆荷白冷眼看着莫离,说:“莫离,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我今天不跟你动粗,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以后别再来用言语刺激小末了。关于你和陈柔谦的这件事上,她已经做得很豁达了,你又何必步步相一逼一呢?如果你真的心有不甘的话,以前为什么要做对不起小末的事情?你跟陈柔谦搂在一起你侬我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小末的心也是肉长的?”
莫离黯然的低下了脑袋,脊椎仿佛一下子被什么人一抽一走了似的,忧伤地靠在门口一侧biubiu那安逸的小窝上。面对这种鸠占鹊巢的卑劣行径,表面上看起来很威武的biubiu竟然屈服了,呻一吟着藏到了夏小末的身后。
夏小末摸一摸biubiu的脑袋安慰它,等她再次仰起头来的时候,莫离漂亮的眼里溢满了泪水。那是她第一次看见莫离在自己面前掉眼泪,她的心竟然很不争气地疼了一下。然后,她看见莫离缓缓地将目光转向埋头一抽一烟的陆荷白。陆荷白把点燃的两根香烟分给他一支,语重心长地叹了口气,以前只知道这家伙见不得女人的眼泪,现在才明白对于男人他一样不能免疫。
“陆荷白,我今天不是来跟你抢女人的……”他的声音很压抑,每次说话,都会有一丝淡淡的烟雾飘出来。夏小末以前最喜欢他身上的味道,说是淡淡的烟草混合了清香型洗衣粉的味道,眼睛一闭,用力一吸,闻起来特别让人沉醉。
“我只是……想求你们原谅我一次,那次的事情我真的不是有心的,陈柔谦也不是你们说的那种女生。”
“嘁。”到了现在这地步,他竟然还有心情说这种话,夏小末冷笑一声走上前去,象征一性一地拍一拍他的肩膀,“莫离,其实我们之间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的,我在你那里也就是借宿几天,归根结底你是那房子的主人,你想往里面塞什么人,碍我什么事啊?根本就轮不上我原谅你。至于陈柔谦到底是什么人,思想高超抑或品德低贱,到现在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你这不就跟她住在一起了么,好歹给了人家一个名份……”
莫离后来就没再说一个字,估计是被夏小末噎着了,那一话里的每个字就像钢珠似的,扯着耳朵倒进去,估计够他消化一段时间的。
最后,莫离站起来说了句再见,沉默地推门离开。
夏小末觉得这家伙挺有礼貌的,出门还没忘记把门带上,然而这门一关,就彻底的把两个人的那些美好记忆与残酷的现实隔开了。想到这里,夏小末猛地把陆荷白推到门外,然后背靠门板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