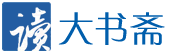跟-我-读eN文-xe学-L楼记住哦!纵有满腹疑问,也抵不过极度疲惫袭来,明兰扎进绵一软温暖被窝,倒头便睡,这回什么梦也没做;一团一哥儿挨她怀里小声一抽一泣,不一会儿也睡了过去,小一脸上还留着泪痕,熟睡中,短小手指无意识勾着母亲袖子。跟-我-读eN文-xe学-L楼记住哦!
母子俩睡昏天暗地,醒来已是午时三刻,正是菜市口开张吉时。
一团一哥儿忽懂事许多,醒后不哭不闹,翠微喂一口他吃一口,只是缠明兰紧,谁来抱他都是满眼戒备,小手抓牢母亲衣裳。奈何满府事等着明兰,她只好哄着小胖子道:“咱们去看姐姐罢,姐姐手痛很,你去帮姐姐呼一呼好不好?”
小胖子睁着黑白分明大眼睛,小小迟疑了会儿,才乖乖点头,由翠微抱至偏厢蓉姐儿休息处。随即,各路管事忙不迭上前,照顺序静候廊下,轮流回禀诸般事宜。
一一夜混乱,半宿大火,损失不可谓不大。
老宅处报销了十之七八,好祠堂安然无恙,顾氏先祖当初将之建于偏僻一阴一润处,明兰颇觉有见识;可惜另一边就无此好运,整片山林俱毁。可叹那刚绽出花一蕊红梅,才结出青翠可一爱一小果桃林,还有花大银子移来几排秀丽花树——统统化为焦木。
搜捡林中时,还发觉几具烧焦一尸一首,明兰正心疼那些被无辜烧死鹿儿鹤儿,没好气叫人拿破草席裹了,连同门外留下贼人一尸一首,一道送往顺天府衙。
除这两处,澄园余处倒无大损伤——不算葛一妈一一妈一惊慌中烧塌半座灶台话。
房屋山林损毁再重,到底是死物,终有修复之日,真正可惜后头。
细细点查后,此夜侯府家丁护卫共伤亡三十二人,其中轻伤十四人,重伤九人,其余……已入往生道矣。明兰嘘叹不已,吩咐郝大成厚葬亡者,并重重抚恤其妻儿老小及伤者。
明兰每说一笔,夏荷便提笔往册子里录入,一旁绿枝算盘打噼啪响,脸色比明兰还难看——略略估算下来,光抚恤金就要出去上万两!
待诸管事回禀毕,鱼贯出去,绿枝面一皮已青跟西瓜皮般了,明兰只好安慰她顺带安慰自己:“……你细想想,昨夜若无人拼死抵挡,咱们早做鬼了!如今雨过天晴,喝水不忘掘井人,不能寒了下头人心。”
绿枝勉强点点头。
话虽如此,可算上来日复建宅邸经费,这几年明兰认真理家所积攒银子几乎要去一大半——呀呀个呸,还真TM如伯虎兄所言,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
明兰捂着胸口心疼了半天才缓过劲来,不等缓过一口气,眼见日影西斜,外头忽来报,道英国公府使人来传话。
“昨夜张家并未受贼人进袭?”明兰听了消息,惊疑不定。
传报媳妇子站门边,提声道:“正是。张家昨日一一夜太平,是以张夫人也未料到咱府光景,今早一听说,就赶忙派人来问安。”
明兰又问:“那国舅府呢?”
那媳妇子道:“来传话人说,眼下外头还戒严着,音信不通,个中情形……也说不清。”
明兰默了许久,她心中存了一一夜那个疑问,已浮起一个愈发清晰答案。
此后,她又召了外院几位管事问话,继续理事,屠龙神色疲惫来禀府内已清理干净,前后门外也再不见贼人踪影,郝大成和廖勇家已分派仆妇杂役收拾整顿院子房舍云云……足又忙了一个多时辰,明兰方才空下来,想及蓉姐儿,她赶紧起身,叫人扶着去偏厢看望。
刚要迈出门,却见小桃颠颠从外头跑回来,口角含蜜,一脸叫人想一抽一幸福样;明兰驻足斜眼,拖长调子:“回来啦——?石二公子伤情可好。”
小桃半傻不呆道:“伤?哦……石头哥只皮肉破了几道口子,屠大爷说不碍事。”
明兰一阴一一阳一怪气道:“那你怎耽搁到这会儿才回?”主母都睡醒理事毕了,贴身大丫鬟还不见人影。
小桃难为情道:“石头哥说……他说,昨夜真吓人,血花四溅,前门后门地上都是死人,他想起来就心头砰砰跳呢,怕都不敢闭眼睡觉!”
屋里还秉笔对账绿枝听得一阵恶寒,险险一头栽进砚台里去,扶着明兰夏荷明显晃了晃,咬唇忍耐再三,终忍不住:“这话你也信?”
小桃愣愣道:“石头哥干嘛骗我?”
夏荷没算计,自然脱口道:“提刀杀人都不怕,哪会怕做恶梦!他诓你呢,他喜欢你,想跟你多待会儿!”
小桃顿时粉面绯红,结实有力胖胳膊‘轻轻推了’她一把,娇嗔道:“哎呀,什么喜欢不喜欢……你,你真讨厌!”又对着明兰含羞道,“夫人,我去帮绿枝了。”然后扭着圆乎乎身一子往屋里去了。
夏荷被推了个踉跄,差点脑门撞门框上,明兰好心扶了她一把,怜悯道:“别和这丫头斗嘴,也别拿石家小子说事,只有你憋气份儿。”
那小两口子,一个无知者无畏,一个脸皮至厚无敌,真是天打雷劈天作之合;明兰又思忖着,不若回头就给石家夫妇去信,待生下腹中胎儿后,便可筹备婚嫁了。
想及小桃此后要远嫁江淮,明兰不禁心头酸酸,默默低头走路,没几步便到了偏厢房,听里头隐隐传出孩童说笑声。
跨门左向转里,走进里屋,却见蓉姐儿坐躺床头,床榻里侧是盘着胖腿扒姐姐身上一团一哥儿,外侧是坐床沿娴姐儿,窗下小几两旁分坐着邵氏和秋一娘一,崔一妈一一妈一独坐如意圆桌旁,轻轻吹着一晚黑漆漆药,额头上尚贴了两枚活淤化血小小梅花形膏药。
见明兰进来,众人面色各异。秋一娘一微笑着起身行礼,谁知邵氏比她起得,兔子似从座位上跳起来,一脸惶恐不安模样,活像又死了一回老公。明兰朝秋一娘一点点头,看也不看邵氏一眼,径直朝床边走去。
蓉姐儿原正愁眉苦脸望向崔一妈一一妈一手中汤药,见了明兰,欣喜道:“母亲,你来了……”说着便要起身。明兰忙上前按住她,柔声道:“起来做什么,赶紧躺着。”又问伤处疼不疼,有否旁不适,蓉姐儿摇摇头,“吃了大夫药,都不疼了。”
明兰心中怜惜,心想待药一性一过去,定然疼厉害。她拂开女孩浓密额发来瞧,只见额后两三寸处,一块糊满了墨绿色刺鼻药膏头皮,犹隐见几分渗人血赤糊拉,她叹道:“亏得你生了这么一把好头发,若换了头发少,怎么遮得住伤处。唉,伤得这样,少说半年不好带金珠钗环,沉甸甸坠得头皮疼。”
蓉姐儿摸一摸自己脑袋,大大咧咧道:“娴妹妹说了,反正我梳坠马髻也不好看,以后索一性一都梳正髻好了;前头母亲不是刚给我一盒子鲜纱堆宫花,不妨事。”她脸蛋偏英气端正,每每梳那种柔美一爱一娇鬟髻,都是各种别扭。
话题说到娴姐儿,却见她一改往日**黠,自明兰进来,始终低着头,听了这话方才微微抬头,小心瞥了眼明兰。
明兰伸手轻一抚女孩脸蛋,温和道:“你俩就跟亲姐妹一般无二,有你蓉姐儿身边开解着,我就放心了。”
娴姐儿目中含泪,稚一嫩面孔带着早熟羞愧,轻轻点头。一旁邵氏张嘴欲言,对上明兰望来冷淡眼神,立刻哑了,她有心想说些歉意话,当着满屋人面却不好启齿。
明兰转回头去,拾起蓉姐儿缠满纱布左掌细细端详;事后她曾检视那贼人匕首,端是锋光锐利,幸亏女孩一性一子刚烈,倔强急怒之下索一性一死死握住刀刃,那当口倘若松了一松,锋刃滑一动之下,怕是整只手掌就要对开了。
饶是如此,依旧是刀刃入骨,皮肉绽裂,直看得明兰心惊肉跳,照大夫说法,以后就算创口痊愈了,手掌怕也不如以前灵活了。
“待过几日戒严解了,我就给你们先生去信,唉,好伤是左手,写字什么倒是不碍,可刺绣…可怎么好…”大幅绣品撑方框立架上,需一手上针一手下针,两手翻飞引线,“说不得,洪大一娘一功课是没法做了……”
蓉姐儿一喜,脱口道:“真?我不用再与洪大一娘一学了?哎哟……”未等说完,被铺下头就被一根手指戳了下,见娴姐儿用力得看了自己一眼,蓉姐儿心领神会,立刻低头,语气虚弱道:“辜负了大一娘一悉心教导,女儿很是过意不去。”
明兰本是满心愁绪,见此情形也不禁扑哧出来。
表情转换扭曲,语气折入生硬,加之配合失调,与自己当年那行云流水般演技是差远了。想当年她们姊妹斗法之时,便是居末如兰也远胜这小一姐俩,别说戏骨级别墨兰和自己了。果然有竞争才有进步么?
两个女孩见明兰笑话,双双低下脑袋,满是赧然懊丧,明兰笑着拍拍女孩们小一脸蛋:“嗯,这么着就好多了,有些像样了,回头就做这般形容给你们先生瞧。”
这话一说,全屋子都笑了起来,崔一妈一一妈一停下凉药羹匙,摇头莞尔,娴姐儿乐倒蓉姐儿肩头,小一姐俩捂着嘴悄声说笑,秋一娘一上前两步,凑趣道:“还是夫人知道,读书看帐什么,全难不倒咱们大姑一娘一,只那针头线脑恼人!”
明兰微笑道:“女红本为怡情养一性一,端显妇德工品而来,我们这样人家闺女,也不见得非练成一精一不可,不然,叫那绣一娘一做什么去。”这话说自有一番老成持重味道,她心中颇是自得,想了想,添上一句,“刺绣什么就算了,不过寻常缝补总得会些。”又转头与秋一娘一道,“你辛苦些,细细教与姐儿才是。”
蓉姐儿连忙将头点跟拨一浪一鼓一般,娴姐儿捂着嘴,拿手指去刮她脸蛋偷笑,秋一娘一也忙表态道:“夫人放心,这原就是我本分。跟-我-读eN文-xe学-L楼记住哦!”这话其实不妥,妾侍本分应是伺候男人和大妇才是,然而时至今日,她已很自觉往老一妈一子身份上靠了。
明兰微微一笑,又问崔一妈一一妈一头上伤势如何,崔一妈一一妈一连声说‘无碍’。
秋一娘一乖觉很,见明兰犹自皱眉,自发补充:“大夫给崔一妈一一妈一开过药后,说现下瞧着是不妨事,待过一阵子再来瞧瞧。”
明兰点点头,其实照她意思,好去拍个片子才保险,可这年月哪来x光,只好吩咐崔一妈一一妈一多歇息了。
见受了嘉许,秋一娘一越发卖力,又道:“今儿晌午我已去瞧过眉姨一娘一了,正坐着给小哥儿喂一奶一呢;母子俩都神气好很。”
明兰展颜道:“这就好,不然我可没法子跟公孙先生交代了。”
昨夜一场大乱,几乎人人都被波及,不是受了惊吓,就是皮肉吃罪,谁知安然无恙,反是平日不大靠谱秋一娘一和若眉。
自打这两人搬至邵氏院里厢房,其实都惊惧得厉害。
贴身伺候若眉两个婆子早得了主母吩咐,又素知这位身娇肉贵姨太太敏一感多思,想与其叫闹不太平,索一性一熬了碗浓浓安神茶,神不知鬼不觉掺汤药中送下。
若眉一觉睡到天亮,压根不知夜里何等刀光剑影,待醒来已是雨过天晴,自己神清气爽不说,儿子也一乳一母怀里睡得小一脸扑红,一大早,母子俩就一精一神抖擞吆喝着回自己院了。
明兰大是赞赏这俩机灵婆子,连同一乳一母内,三人均各赏十两银子。
至于秋一娘一,屋里倒是惴惴了一一夜,当蓉姐儿不见时,她本想去寻,却被婆子吓住。
“姨一娘一又忘记夫人吩咐了么?夫人特特对姨一娘一说过,不论发生何事都不许离屋,姐儿不见了,自有丫鬟婆子去寻,姨一娘一若非要去,到时一个寻一个,都走丢一了,反倒坏事!”
因近来被明兰冷着脸收拾了一阵规矩,秋一娘一畏惧主母威仪,便老实待屋里,不敢自行走动,只竖一起耳朵听外头动静——前半夜无事,后半夜热闹。
刀剑打斗之一声就庭院门口,夹杂深夜回响惨叫一声,吓得她几乎腿软失一禁,差点要跳窗而逃,谁知没等她鼓起勇气去开窗,贼人就被守院外护卫收拾干净了。
再接下来,护卫们使婆子进来报平安,她和丫鬟们松口气后,见天色微亮,深觉身心俱撑不住,便各寻屋子去歇息了。从头至尾,秋一娘一纯属心灵受惊,**十分安全,当做听了个吓人鬼故事罢了。
“……都说昨夜凶险,可我们连贼人是圆是扁都没瞧见。”说到后来,秋一娘一也不全是给主母拍马,心中真感激明兰周全保护,“眉姨一娘一叫我代向夫人磕头谢恩,说多亏了夫人筹谋妥帖,他们母子才能平平安安,头发一丝儿都没伤着。”
说这话,她并无讥讽之意,可邵氏依旧羞愧上涌,脸上变了好几霎颜色,终忍不住,上前道:“…弟妹…我,我…都怪我糊涂…险些连累了一团一哥儿…”说着便红了眼眶,拿帕子捂着眼睛,“倘哥儿有个好歹,我,我真是没脸见你了…”
没脸见我?
明兰心中冷笑,好轻飘飘一句话,若她真害死了儿子,自己活吃了她心都有!
“大一嫂子有何错?人心百态,本是各自肚肠,大一嫂子信不过我,想自行寻个藏身之处,也是理。”这话说得既尖又酸,听得娴姐儿难堪低下头。
邵氏发急,不住赔罪。明兰故意晾她一会儿,想听她还有什么可说,谁知邵氏口齿不利,肚里也没深度,翻来覆去就那几句‘我糊涂,我不好’,言辞既无甚出彩,眼泪流得也不够真切可怜。连娴姐儿也听得暗自摇头,深觉这种说辞如何叫人谅解。
邵氏一抽一泣了会儿,原想着弟妹素来脾气好,就算心里还有气,当众人面也会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吧,谁知左等右等,不见明兰开口说些宽宥话,只不冷不热架开话头,反转头去逗一团一哥儿顽,她不由得尴尬站当地。
明兰只能再次感叹,盛家可真出人才呀。
今日倘换做是林姨一娘一,遇上这种自请罪场面,包管可以从自怜身世一直哭诉到天地苍茫,满目望去无可依靠,这才做出糊涂事——直说得闻着伤心见者流泪,怜卿命薄甘做妾,后忘光她犯错。
心中暗暗摇头,明兰不再耽搁,又吩咐了蓉姐儿几句,方对邵氏道:“有件事,本想过几日再说。既见大一嫂子一精一神好了,不若今日一并了结了罢。”
邵氏心头乱跳,强笑道:“何…何事…?”
“还能有什么事?任姨一娘一呗。”明兰慢悠悠转身站起,“领着贼人满园子走,多少双眼睛看见了,总得有个交代罢。”
说完这话,她扶着夏荷率先走出屋子,邵氏脸色惨白,摇摇欲坠,几有推脱不愿去之意,侍立旁夏竹忙上前,一把托住邵氏胳膊,半扶半拖着跟去了。
一行人绕行至后座抱厦,从偏侧门直出嘉禧居,沿着一条一卵一石铺就小路朝北走去;明兰捧着肚皮,一晃一摇走得极慢,邵氏不敢催促,只能熬着一性一子亦步亦趋跟后头。
其实也没走几步,邵氏却恍觉隔世,生生熬出一脑门汗来。一行人来到后排屋靠西厢房,里头无甚摆设,只一张圆圆如意桌,桌旁三四张凳子,窗边架了个极大花盆子,里头泥干草枯,显是许久无人料理了。
夏荷轻声道:“仓促之间,只来得及粗一粗洒扫了下,夫人别见怪。”
明兰来回看了圈,见窗明几亮,地面一尘不染,满意道:“也就用一会儿工夫,费什么劲,这样就很好了。”她边扶着圆桌坐下,边道,“别磨蹭了,赶紧叫人带上来吧。”
夏荷应声而去,夏竹见状,一把将邵氏甩凳子上,赶忙绕过桌子,转到明兰身旁服侍。
过不多时夏荷回来,后头跟进来三拨人,当头是屠虎,其后是两个侍卫夹一着个捆一绑手脚妇人,后是两个婆子拖着个缚牢丫鬟进来。侍卫将那妇人往地上一丢,然后抱手戒备两旁,两个婆子有样学样,将那丫鬟也摔明兰跟前。
邵氏低头望去,只见地上那妇人生得身形丰一腴,秀丽杏眼被打青了一只,形容狼狈,鬓发凌一乱,衣衫上滚着许多泥泞,不是任姨一娘一又是谁?
至于地上滚另一个,自是碧丝了。
邵氏抚一着胸口,犹自惊疑不定,却听明兰微笑道:“屠二爷自昨夜辛苦至今,正该好好休憩,这事交由旁人便可,何必亲自来?”
屠虎笑道:“外头已清理干净了,赶紧料理了这个,大家伙儿才好放心歇着。”说着,弯腰扯去那妇人嘴里塞布一团一,“夫人,您问话罢!”
碧丝也被堵了嘴,只能发出呜呜低鸣声,仰脖望着明兰,目中流露出哀求之色。
明兰不去看她,反转头向邵氏,笑道:“我有什么可问呀!这是大一嫂子身边贴心人,还是嫂嫂来问罢。”
邵氏脸上发一热,不敢抬头看对面三个彪形大汉,只能去盯任姨一娘一,弱弱道:“…我,我…你为何要引贼人进来…”无论一娘一家婆家,她从未掌管过庶务,问起话来毫无威势,越说越轻。
任姨一娘一一见邵氏,当场涕泪滂沱,哭嚎道:“夫人,我冤枉呀…我哪敢…是那贼人要挟…拿刀架我脖子上呀…”
话还未说完,明兰便笑了,“我说,任姨一娘一,糊弄人也得看地方。你瞧瞧眼下架势,是你忽悠你家夫人就能过关么?”
任姨一娘一闻言,环视了屠虎及两个侍卫一眼,瑟缩了身一子。
因邵氏守寡,她身边媳妇丫鬟也跟着往暗沉老气上打扮,平日不许涂脂抹粉,不叫佩钗戴环,明兰以前没留心,此时细看,饶是一眼乌青,两颊高高肿起,依旧难掩这任姨一娘一姿色不俗,“是受要挟才引贼人去蔻香苑,还是里通外贼,你当旁人都是瞎子不成?”
任姨一娘一心知明兰不比邵氏,是个厉害角色,可到底存了侥幸,嘴硬道:“黑灯瞎火,兴许有瞧错……”又扭一动被捆牢身一子,冲邵氏连连头点地,“夫人,咱们相伴这么多年,您可要为我做主呀!”
邵氏嘴唇动了几下,目光触及明兰寒霜般面庞,嘴里话又缩了回去。
“好个不见棺材不掉泪东西!”明兰冷哼一声,“好,就跟你说个清楚。”
她左手向邵氏一指,“你们夫人素日清净度日,两耳不闻窗外事,她怎会知道我将一团一哥儿藏于何处!你们屋邛一妈一一妈一说了,是你报大一嫂嫂知道,又一劲撺掇她查个究竟。”
邵氏面如滴血,头几乎垂到胸前,任姨一娘一张口结舌,明兰冷笑道:“我自负行一事也算隐秘了,竟叫你探得了风声;哼,你可别说是顺耳听来!可见你平日用心之深!”这种事不是平日闲磕牙能探知,必得时时留意嘉禧居动静方可。
任姨一娘一颤着身一子,虚软道:“…我,我是为了夫人和姑一娘一,才一直留意…”
明兰不去理她狡辩,继续道,“你说动大一嫂子后,趁外院大一团一之际,将碧丝叫去跟前问话。大一嫂嫂不善言辞,只坐上头,是你旁巧言善语,诱以重利,终问出底细来。”
捆成虾米状碧丝用力扭一动,发出呜呜叫一声,双目如同喷火,恨恨瞪着任姨一娘一;任姨一娘一终归不算老练作一奸一,竟不敢去看碧丝目光。
“好!就算你适才说不错,你是为主子才留意我院里情形,既打听出一团一哥儿下落,你就该跟大一嫂嫂她们一道过去躲藏,贴身护主才是!结果你跑哪儿去了?”
明兰满眼讥诮,质问连连,任姨一娘一都答不出来。
“你借言内急跑出去,先遇上了暖香阁阎婆子,你说去给大一嫂嫂叫些宵夜,阎婆子说,彼时两侧均未起火。接着看二门崇一妈一一妈一瞧见你往西奔去,其时东侧老宅已火光冲天了;后是看林子福伯,那会儿西边山林刚起火。”
明兰逐渐提高嗓门,语气愈发凌厉,“你一个内宅妇人,大乱时往外院林子那儿跑什么,摆明了去接应贼人!且昨夜凡是见过你人,都说没什么刀架你脖子,你还敢狡辩不成?!”
任姨一娘一被一逼一问手足无措,一旁屠虎露出残忍神气,一阴一□:“夫人何必跟这贱婢多说,交到俺手里,把她骨头一根根拆了,看她说是不说!”
明兰摆摆手,她是时代法制人员,总要先礼后兵嘛。
任姨一娘一惊惧不已,如同痉一挛了般一团一起身一子,拼命挪动得离屠虎远些,尖声叫道:“二夫人饶命!我都说了,再不敢抵赖!”
明兰冷冷看着她:“你晓得我想问什么罢。”
任姨一娘一咬了咬嘴唇,忍着手足麻痹,颤声道:“…是太夫人那边…那边使人来找我。”
明兰闭了闭眼睛,喃喃着:“我猜也是她。”
“…不,不止是我,外院也有太夫人人,说好到时开门放人进来,谁知两位屠爷临了从庄上调来许多丁勇,又亲自盯紧前后大门,没机会下手。”任姨一娘一断断续续道。
屠虎听得勃然大怒,吼道:“是哪个吃里扒外兔崽子!”
任姨一娘一吓肝胆俱裂,忙道:“是…是门房韩三…”
屠虎一愣,“韩三……?可那小子昨夜中箭死了呀。”随即又一把提起任姨一娘一身一子,吼道,“莫不是你为着脱身,胡乱栽赃!”
任姨一娘一杀猪般嚎丧起来:“真是韩三!真是他!原本我只管探消息,谁知昨儿入夜前,韩三偷传消息给我,说情势有变,两边大门怕都开不了,人放不进来,叫我打听了一团一哥儿藏身之处,就去西边林子那儿接应!”
屠虎手一松,晦气大骂道:“居然叫眼皮子底下掺了沙子!”又朝明兰连连谢罪。
明兰啼笑皆非,人都已经死了,任务也没办成,又有什么可说晦气;屠虎犹自气愤,直说查清后,要抹了给韩三家眷抚恤银子。
邵氏默默听了许久,此刻终于忍耐不住,冲着地上哑声道:“…我,我们自小一齐大,又共侍一夫,我往日也待你不薄,你为何要…”
任姨一娘一本缩地上低低哭泣,闻言忽如火山般爆发了,她用力直起身一子,怨毒瞪着邵氏,吼叫道:“你还敢说待我不薄!都是你害!都是你!你这假仁假义蠢妇!”
她丰满胸膛不住起伏,粗重喘着气,“……陪嫁过来姊妹都纷纷嫁了,我年纪小,原想到了岁数也能配桩体面婚事,谁知…谁知,你竟把我给了那痨病鬼…!大爷还有几天活头,你自己守寡还不够,还要拉上我!”
邵氏被她一记喝晕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尖声辩道:“你,你怎么敢说大爷是…是痨…?!我生了娴儿后多年没动静,见你有宜男之相,有心抬举你,将来若生下哥儿,你岂非有天大体面!”
“呸,抬举个屁!”任姨一娘一恍若变了个人,飞散着头发,疯叫道,“大爷身一子你不清楚?!到了后头几年,他连行一房也不成,生个屁哥儿!我早说了不愿,你这蠢猪却硬要说我是面一皮薄,怕羞,还颠颠去跟太夫人表功,好装贤惠,结果太夫人直接给我摆了酒……”
想及往事,她泪流满面,“到了那地步,我不肯也不成了。”
邵氏失魂落魄,喃喃道:“原来你真不愿……”她心中,顾廷煜是天下第一好男人,又是侯府之主,加之她平日看听,都是丫鬟想攀上爷们当姨一娘一,怎么……?
明兰旁冷眼看,照理说,顾家前任侯爷一阴一私,不该议论,不过想这对夫妇,一个生前欺负她老公,一个昨夜险些害了她儿子。明兰便不制止,嘴角略带讥讽,静静坐着听了。
“我统共伺候了那痨病鬼不到五回;他生前,你叫我守活寡,他死了,你也不肯放了我!还说什么要跟我相依为命!我才几岁呀,你竟这般狠心!”
邵氏听得手足冰凉,慌道:“我,我是真心想叫府里给你养老,我……”
“放你一娘一屁!老什么老,我这般颜色年岁,还有大半辈子要过呢!”任姨一娘一厉声叫骂,“你自己当寡一妇无趣,想拖个伴儿解闷罢了!”
邵氏被骂天旋地转,欲辩不得,脸色涨得紫红,明兰看得好生解气,直至见邵氏气簌簌发一抖,才悠悠道:“好一张巧言善变利嘴,大一嫂子果然埋没你了。不过我有一问,你与大一嫂嫂相伴多年,岂不知她一性一子绵一软,好说话,你若真想嫁人,跟她直说便是。哪怕惹她心中不,也不见得会罚你,终究会放你出去。你为,怕不是单单嫁个人吧?”
看任姨一娘一脸色忽变,明兰心知自己料中了。
死了男人妾要改嫁,本来不难,但要嫁得好却是不易——正经好人家,干嘛非娶你个残花败柳不可,非得有大笔银子陪嫁,或有旁抬举才成。
任姨一娘一本想嫁侯府中得脸管事,可顾家兄弟交恶,明兰怎会将服侍过顾廷煜妾侍配给得力管事为妻?而邵氏守寡后,想多给娴姐儿攒些嫁妆,将银子看得愈发重了,自己提出改嫁,本就会惹邵氏不,顶多白放了身契,怎么还肯给丰厚嫁妆。
思来想去,还不若投靠太夫人那头,还能博个好前程。
“我……”她刚要开口再辩解一二,就被明兰抬手拦下。
“就算你有苦衷,不得已而为之。”明兰缓缓收回手,“可我从不曾亏待过你,蓉儿姐弟俩也不曾,林边被一刀一捅一死安老伯几个不曾,惨死蔻香苑门口那几个婆子丫鬟不曾!就因你吃过苦头,就能里通外贼,害人一性一命么!”
明兰一掌拍桌上,面罩冰霜,冷冷瞧去,任姨一娘一无言以对,面色如土低下头。明兰转头道:“话都问清楚了,请屠二爷将她交过去罢。”
屠虎早等这话了,闻言捡起那布一团一,再度塞回任姨一娘一嘴里,待那两个侍卫一把夹起任姨一娘一,他领头迅速朝外头走去,只余下任姨一娘一远远传来呜呜叫一声。
邵氏僵原地半,双手紧紧攥着帕子,脸上似是尴尬,似是恼怒,又似是伤心,半响才道:“…她,她将被带往何处…?”
明兰指了指门口,示意夏竹去关门,同时顺口答道:“叫往刘正杰大人手上。”说着,嘴角弯了弯,“咱家是积善人家,便是内贼,也不好随意发落一性一命,还是交给官府办罢。”
邵氏再笨,也听出明兰话中另有深意,顿了顿,低声问:“露一娘一,她…会如何下场…”露一娘一是任姨一娘一名字。
“那要看刘大人审得如何了?若昨夜来袭只是寻常蟊贼,那任姨一娘一也不过落个贼婆子罪名,若昨夜那伙人是反贼同伙,那任姨一娘一……”明兰说面无表情。
作为反贼,通俗下场无非是绞颈斩首之类,若是头目级别,大约还能享受到‘凌迟’这种高技术含量刑罚。
邵氏思绪万千,一时悲一时惧,忽伏桌哀哀轻泣起来,明兰没半分怜香惜玉之心,凉凉道:“大一嫂嫂别急着哭,先把这个结了再说,如何?”邵氏这才惊觉地上还滚着碧丝,两旁还有两个婆子,讪讪揩泪端坐。
婆子得明兰示意,一抽一出堵碧丝嘴里布一团一,碧丝适才听任姨一娘一招供,已知自己闯下大祸,吓得泪水涟涟,甫一松开嘴里,就连忙哭着哀求:“夫人,奴婢知道错了!奴婢该死,求夫人饶过我这回罢!”又连连磕头,满嘴叨扰。
夏荷见她清丽面庞上俱是泥污和血渍,不禁暗自可怜,冷不防听明兰朝自己道:“拿出来罢。”她忙回过神,赶紧从袖中取出一小包物事放桌上。
那是用丝巾包一对镯子,镯身通体赤金,打成滚一圆荷叶宽边钏儿状,上头镶有数颗明珠,璀璨夺目,于镯扣处竟还各嵌有一颗黄豆大猫儿眼。
一见此物,邵氏脸色顿时青红交加,她心虚望了明兰一眼;只见明兰闲闲拨一弄那对镯子,“这对镯子是当初顾家给大一嫂嫂聘礼罢,果然好东西。”
邵氏哪敢答话,只胡乱点了点头。
“就是为了这对镯子,你就把我和一团一哥儿卖了?”明兰声音轻柔。
碧丝抖得筛糠般,哭道:“不,不是…我见是大夫人,素日夫人多信重大夫人,想着告诉大夫人也无妨…”
“崔一妈一一妈一是怎么跟你说?别说是大夫人,就是天王老子,也不得透半个字。”明兰语气淡漠,“这些话,你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碧丝无话可说,只能不断磕头求饶,又去瞧夏荷和夏竹,盼她们代为求情。
夏竹心软,耐不过就想开口,却被夏荷扯了下衣袖,制止下来。
不是夏荷心硬,而是她清楚主母一性一子,但凡明兰拿定主意事,鲜少有人能改变,何况——她看了周围一眼,缓缓低下头去。
今日这种场面,明兰却带她与夏竹来服侍,是什么用意?
小桃远嫁即,绿枝也到放出去岁数了,不过这一两年,嘉禧居大丫鬟便要全部易位;翠袖和春芽倒讨夫人喜欢,可年纪还太小,那么剩下就是……夏荷心中通透,暗自决心近要用心当差,少自作聪明才是。
明兰望着连连磕头碧丝,心中伤感,“你自小就没什么大志向,既不聪明灵巧,也不够忠心勤,只消给你好吃喝好穿戴,你就知足了。”这要搁现代,倒是个极安分守己二一一奶一材料,绝不会生出晋级野心。
“你我身边,何尝有几分做丫头样子,整日好逸恶劳,拈轻怕重,亏得丹橘她们宽厚,不与你计较。可我虽不喜欢你,可到底一处十年了,人非草木呀。”
都说喜欢回忆,就表示开始变老,明兰忽觉一醒扬州梦,往事历历目,一次次背叛伤害,一次次离去分别,回头望去,惊觉自己已老了。
“不过,你却也没惹过什么麻烦。”碧丝一性一子懒散,既不像若眉目下无尘,也没有燕草心眼儿多,早早惦记好了前程。“我原想着,待小桃绿枝出了阁,就给你找个会疼人,家底殷实嫁过去,叫你一生保暖,咱们一场主仆缘分,也算善始善终了。”
碧丝满心慌乱,不知明兰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忽听叮咚轻响数声,眼前金光珠闪,原来明兰将那对镯子连着丝巾丢自己跟前,耳边传来明兰冷淡声音。
“我不来罚你,也不打骂你。不过,咱们缘分算是了。”明兰轻叹,“记得你家中尚有兄嫂和老母,我这就放你家去。这镯子给你,你这些年攒银子珠帛也统统给带走,不论买些地,或收间铺子……终归,以后你好自为之罢。”
说完这句,明兰便朝那两个婆子挥了下手。
碧丝耳边嗡嗡作响,只听得‘放你家去’四个字——
不要!她不要回家!自打祖父和父亲接连过世,家中一日不如一日,才将自己卖入盛家,老母软弱,兄长无能,嫂嫂又刻薄;何况家中清苦,要一操一劳家务,一个铜板都得计较再三,哪及明兰身边锦衣玉食,十指不沾一阳一春水,悠闲度日。
她当即就要大哭告饶,谁知那婆子出手如电,嘴里迅速被塞回布一团一,什么也说不出了。
她拼命挣扎,呜呜狂叫,不断用眼睛向明兰求饶,只恨那两婆子手似铁钳般,拿捏得她动弹不得,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从明兰跟前拖走。
直至到门外,其中一个婆子轻声讥讽她道:“我说小姑一奶一一奶一,好歹消停罢!你还当自己是金贵主子呢。”另一个道:“夫人也是忒仁慈了,这种贱婢,险些害了小主子一性一命,照我说呀,还不远远发卖了才解气!”
冷言冷语断续传入屋中,夏荷眼眶酸涩,这两年她与碧丝同住一屋,朝夕相处,纵不算情同姐妹,见她这般下场,心中也是难过非常。她此刻想着,待以后自己能进出容易了,便去常探望碧丝,好周济一二。
谁知事与愿违,若干年后她嫁了个颇有才练小管事,随后跟着夫婿到南边替顾家经管田庄,一去数年,再见碧丝时,已十年之后了。彼时她,几不敢信这个面红高嗓,粗手大脚鄙陋壮妇,竟是曾经那个腰纤如柳,喜滴翠色,好风雅事闲散女孩。
发落碧丝后,明兰也是情绪低落,片刻后才道:“夏荷,你去给她收拾行囊,一针一线都给她带去,别叫旁人贪了。夏竹,你去外头看着,我要与大夫人说会话。”
两个女孩低声应了,一个直出门而去,一个轻手轻脚从外头带上门。
此时屋内只余她们二人,邵氏整个人都绷直了,如惊弓之鸟般坐卧不宁,瞥见明兰正不错眼盯着自己,她加慌了:“弟妹,你别吓我,这回是我错了!是我不好…我…”
听了任姨一娘一招供后,认错话虽还是老调重弹,可心意却真诚了几分,每个字俱是发自肺腑。
“大一嫂究竟哪里错了?”明兰一逼一问道,“是不该听任姨一娘一撺掇,还是不该不听我话?”
邵氏一下就被问住了,顿时憋脸色黑红。
“我来给大一嫂子号号脉罢。”明兰步步紧一逼一,“大一嫂错处有二,一者,不肯信我;二者,又太易信旁人!归根结底,大一嫂子就是信不过我,任姨一娘一说我拿你们放明处,是做了一团一哥儿幌子,你其实很信罢!”
邵氏哪敢应声,只能连连摆手:“不,不不…哪能呀…”
“我说个明白罢!”明兰一拍双掌,撑着桌面立起来,“京城大乱,会来侯府捣乱无非两种人,不是为财,就是别有用心之辈。我特意叫人将嘉禧居主屋点得灯火通明,为就是好引贪财蟊贼过去,哼,满府还有比我居住财帛丰厚地儿吗?蟊贼抢完我屋子后,怕是连走都走不动了!”
邵氏张大了嘴巴,结巴道:“我,我就说,怎么你院子亮堂成那样……!”
“若是冲人来……哼,侯爷两兄弟不睦,闹过何止一回,半个京城都知道!无论宫里来捉拿,还是咱们那好继婆母,都只会冲我们母子,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好罢,若非要进去……你那院子可是挨着湖建!四面里倒有两面半是临水,难不成贼人还能随身带筏子来夜袭?!统共只一处出口,易守难攻,我布置了多少护卫呀,屠老大早说了,除非冲进三倍数贼人,否则绝进不去!”
明兰双掌撑桌上,气势一逼一人,吓得邵氏几欲钻桌下了。
“老实跟你说,我心中防备,其实就是太夫人那头!反贼那头又不是她开,能来捣乱人数也有限,我怕是明一枪一易躲,暗箭难防!这府里使唤着多少先前老人呀,人心叵测,府里乱作一一团一时,婆子丫鬟们进进出出,一根簪子一包药,一块石头一根刺,一团一哥儿才多大,能防得住么!可事发之前,这种诛心话我能说么!”
邵氏欲哭无泪,几乎要给明兰下跪了,她瘫一软桌上,哀求道:“弟妹,是我猪油蒙了心,有眼无珠,不识好歹,若,若真…我给一团一哥儿赔命罢…”
“我不会叫大一嫂子赔命。”明兰冷冷道,“我素来喜欢娴姐儿,便是侯爷不喜,我也有心给她将来谋个好前程。可一团一哥儿若真叫你害死了,我觉着我会怎么想?”
邵氏猛一个激灵,双手乱摆:“不,不…这不干娴姐儿事…”她忽然万分感激蓉姐儿,若不是她抵死救弟,便是她们母女活了下来,怕以后日子也难过了。
“好险呀,只差那么半步…”明兰目中流露深切后怕,“若非蓉丫头刚烈果敢,一团一哥儿已送了一条小命了。此刻什么情形,真是不堪设想。”
邵氏不敢往下想,不说明兰,便是顾廷烨怒火就能将她们母女活烤成灰烬还富富有余了——她越想越怕,一时间手心背心俱是冷汗。
明兰冷冷盯了她良久,方才道:“我今日这么说,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娴姐儿。”
邵氏木头人般抬起头,不明其意。
“你偷去蔻香苑躲藏时,只想带娴姐儿一个吧?”明兰叹道,“娴姐儿是好孩子,那当口居然还记着蓉丫头,将她一并叫了去。”
邵氏顿时泪盈出眶,仰头哭道:“我好闺女!一娘一险些害了你,你却救了一娘一呀!”
娴姐儿叫去了蓉丫头,蓉丫头救了一团一哥儿,间接又救了自己和母亲处境——冥冥天意,果是善有善报!她心中忽升起万分虔诚,对天道神明,对因果循环。
明兰推开门,临跨出去前,肃声道:“大一嫂子放心,只要嫂嫂今后不再犯糊涂,我会把两个姑一娘一全当亲生闺女看待。”顿了顿,“我说话算话。”
说完这话,她再不回头,扶着守门外夏竹,径直离去。
当晚,用过饭后,绿枝来报邛一妈一一妈一递过来消息——邵氏已将前因后果与娴姐儿说了,母女俩抱头痛哭了一阵,邵氏虽自责不已,却也放了心。
次日一早,娴姐儿顶着红肿眼睛来给明兰请安,不安扭手挪脚,明兰怜惜摸一摸她脑袋,叫她去跟蓉姐儿和一团一哥儿顽了。
不过对着邵氏,她可没这么好脾气了。虽依旧礼数不缺,但神色肃穆冷淡,一句多余也不多说,直把邵氏吓得唯诺服帖。
明兰曾想过,倘若之前邵氏就畏惧自己如同畏惧太夫人,哪怕任姨一娘一再起劲撺掇,大约邵氏也不敢冲去一团一哥儿藏身之处罢——秋一娘一就是极好例子。
小人畏威不畏德,春风化雨不是对所有人都管用。
对这无奈现实,明兰唏嘘不已。
作者有话要说:
表骂偶,表骂偶,没有别理由,就是写不出来。
怎么想也觉得结尾不妥当,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
不要乱猜别理由,出版什么绝对网络之后——为了表示歉意,后面几篇番外,偶会以免费形式贴出来。
鞠躬,对不起。
真是写不出来呀,杀了我头也写不出来。
跟-我-读eN文-xe学-L楼记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