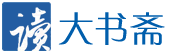二更鼓响过,冬梅在床上翻来覆去,浑身一骚一痒难奈,白日之事恍在眼前,几次欲起去后园幽会金良,又暗恨自家不争气,如此粗劣男人亦让自家神魂颠颞倒,偏偏这恼人春夜,叫人怎能独眠?肉一欲人情,非礼规所能禁,个中滋味,怎忍割舍,胡思乱想间,褥子已被洇湿大片,摸生门,早已湿一透!如何消除此难耐欲一火,又要自家摆一弄自家?……罢罢,反正已做了秀才,再中个举人罢。冬梅披衣而起,一精一赤着下一身就往外走,走了几步才觉不妥,返回穿上一套裙,哪管里面空空如也,一路淋一漓不尽,直奔后园而去。
夜阑更深,蛙鸣虫唱,明月高悬,疏星排列。冬梅急急如风,穿越小轩,绕过石桥,曲径通幽,顷刻来到金良房子外面。
冬梅四顾无人,忙又推门,门虚掩着,呀的一声响后,溜进房内,听帐中鼾声如雷,冬梅捺不住心头狂喜,轻手轻脚直奔床前,挑开帐幔,鱼一般溜进金良被窝中。金良不推不拒,迷迷糊糊中用大手去扯冬梅下衣,一摸一精一光,亦不做声,游走不停,腰间那物挺一起,顶在髋上亦不入巷,急得冬梅如泥鳅人泥,乱钻乱摆。大手又至一牝一户抚一摸良久,继而下移,遍梳玉一体之后,欢手摩至肉一缝儿,久久摸一弄,冬梅急得乱骂:“狗杀才!有什么好耍的,还不快快替老一娘一止痒。金良亦不做声,将小脚提起一尺,搁在肩上,扶着家伙往里便一肏一。初时试探花丛,似小和尚般探头探脑,搅得冬梅一阴一水横流,畅快至极,更痒难止,金良用手摸一着一牝一户四周,一阴一气发动,沛然成雨,遂挺身一插,直到花一心深处。喜得冬梅金蓬在半空中连蹬带舞,直是心肝地叫,那金良更是一肏一得虎虎生风,夹带渍渍水声,把个虫鸣蛙叫硬是一逼一退了。当下就一抽一送了一千多下,一肏一得冬梅花一心怒放,一阴一精一频丢。比白日在草地上干更是另一番滋味。
金良早已打过头阵,何惧关隘万险,一路冲杀,马不歇,人更不歇,足足杀了两个时辰亦不怯阵,这边冬梅虽嫩花一枝,初尝风雨亦无所惧,猛掀动身一子极力往上凑迎弄,记不得有多少回合,却不见胜负。一婬一水汗液把个褥子湿一透,连换三块巾帕仍不住手。金良愈战愈勇,那物件暴跳如雷,可怜冬梅花簇般的一阴一户己被捣得水肿不堪,仍在频频接应。冬梅几次都被一肏一得晕死过去,醒来仍不依不饶。金良见一时战不倒冬梅,索一性一拔一出一阳一物用巾帕擦了又擦,又将冬梅横在床上,自家跳下床站稳,掰一开两股,大举侵人。
此时月华透窗,照见二人模样,金良低头看一阳一物在一牝一户中出入之势,甚是有趣,唧唧之一声不绝于耳,冬梅觉小肚子中又多了一截,不禁阵阵一浪一叫,一乳一波一臀一浪一,好不一婬一荡。金良一婬一兴大发,狠命一抽一提,一连又是近千余下,一肏一得冬梅手舞足蹈,声息渐小,冬梅暗忖今晚他竟金一枪一不倒,再弄一个更次亦是无用,不如让他暂泄,杀一杀他的威风,自己亦好休整一下,然后再战,思此不由一浪一声大起,又说些一婬一辞,又摆又摇,前后推拉,一阴一肌收缩,麦齿紧含,把个金良弄得如颠如狂,猛然间狂抖起来,一阵一阳一精一射在花一心深处,似雨打芭蕉一般。冬梅觉一阴一中甚热,一阵眩晕,一阴一精一也出,四肢如废,摊成一团一泥。金良拜倒辕门,气息渐微,死了一般。
有诗为证:
但愿生从极乐国,免却夜夜苦相熬。
二人交一颈叠一股,睡至鸡啼方起,冬梅道:“又便宜你一一夜快活。”金良道:“夜里一浪一叫的是哪一个?”说罢又去抚冬梅光一溜一溜的那处。冬梅一躲,骂道:“昨夜不曾吃够,又来歪缠老一娘一。”金良老着脸道:“姐姐,就是将那一话儿整天插在姐姐的小肚子里那才快活哩。”冬梅又笑问道:“你个挨刀的,做个欢喜佛亦没歪缠在一起哩!”金段又笑问道:“姐姐明晚来不来?”冬梅在他的脸上扭了一把,道:“我才不来哩,你一个人打一手铳罢!”金良趁势搂住冬梅在怀里亲了个嘴,用手摸一着一乳一,道:“我打一手铳能消火,恐怕姐姐无处寻角先生受用,还是找我这根真家伙吧。”说罢又欲求一欢。
冬梅被他这么一捏一摸,欲一火又上来了,跨到金良身上,捻住一阳一物照一牝一里一送,一上一下套一动起来,金良大喜,双手搂住冬梅的蛮一腰,往上顶一送,口里哼唧着道:“姐姐,你的倒浇蜡功夫还不错哩!用力多弄!”冬梅伸手一下将金良抻起,金良坐着与冬梅弄了起来,动情之处,冬梅大呼大叫,一阴一精一丢一了,金良呼一呼喘着卖力一抽一送,不觉龟一头一麻,亦泄一了。二人又倒床床上,良久,冬梅长叹了一声道:“如此下去,怎生得了?”金良含一着冬梅涨大的一乳一头,含混不清的道:“姐姐若依我计,定会无事。”冬梅一把扯住他的一阳一物道:“依你何样一奸一计?”金良笑道:“不错,正是一奸一计,待我俩交一欢之时,让小一姐看见,不怕小一姐不入瓮。”冬梅用力一抓道:“天杀的,真是要骗一奸一小一姐不成?看老爷不打死于你。”金良手指早已抠进冬梅肥腻肉一缝之中,道:“小一姐倘若被一奸一亦不敢告,名声要紧哩”。冬梅拿开手道:“不与你乱讲了,我要服待小一姐去了。快些拿出你的脏手。”金良一抽一出手指,见指上早已黏一液欲滴,遂道:“看姐姐一骚一兴又发,再来一回如何?”冬梅站起身来,惊道:“你这贪吃鬼唬杀我也!”说罢,穿上裙子就走。
金良赤一精一条条下床就追,在门首赶上紧紧搂住,那时节,冬梅裙带还未系上,金良便站着仗着腰中之剑,急寻孔洞刺去,刺得个冬梅面无人色,低低叫道:“天杀的,让人从窗外看见怎生了得?”金良哪管冬梅说什么,将冬梅抵在门上,一抽一送不止,约有二百余下才往了,再看冬梅娇一喘微微,酥一胸半解,如一醉如痴,把个香舌抵送津一液到金良口里,金良挺一阳一物又冲入一牝一中;乒乓乓又大弄了一百余下,正欲狂一肏一,忽听隔房门响,冬梅忙一抽一身提起裙儿。又手理云鬓,再看金良白眼一翻,身一子一抖,龟一头中喷一出些汁液来,落在门上,亦撒至冬梅的裙子上。冬梅急用手摸,黏黏的,米汤一般,不禁笑骂道:“你这些坏水出了,看你还逞什么威风!”说罢,听听无有什动静,系好裤儿,猫儿一般开门潜去了。?
金良回到床上躺定,慵懒之中心满薏足,暗忖道:“不想女人裙下妙物如此让人销一魂,真不枉为一回人!待把那风一骚一的小一姐勾上一床云雨一番,就是死了亦心甘情愿了,待思个计策行一事。”想到小一姐模样,不觉档下又涨硬起来。
且说冬梅一路小跑,回到卧房,关好门,日头光亮亮的在空中,映得满室金黄,冬梅上一床欲穿上内一衣,碰到腿处黏乎乎的好生痒痒,亦不知是金良还最自家流的,遂取过菱花镜,坐在床上,支起雪白的腿一儿,照那私一处,一照之处不觉心寒,只见镜中之物青肿,毫一茎一凌一乱,遂用手理了理,有些烧灼般痛,思无良药,只好穿上内一衣,在房一中闷坐。
这正是:
桑间陌上欢不够,等闻候又迎郎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