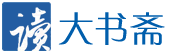金良哪懂什么怜香惜玉,只顾痛快,挺一抽一乱插,可怜冬梅在下面,樱一唇微张,黛眉紧锁,约一抽一了两百余下后,便也不觉如先前那般痛楚了,虽酸一痒异常,似有几百只小虫儿在一阴一中拱起爬去,遂紧搂金良腰背,掀动双股不往往上凑迎。金良又勇力大振,大肆一抽一送了近五百下,到底是一毛一头小子,懂什么养一精一运气,刹时间大一泄,死猪一般不动了。
冬梅正干得兴起,忽见金良一阳一物软叽叽滑一出,心中不免恼恨骂道:“没用的死贼囚!”用力掀下金良,再看地上草间,血水一婬一液弄得秀草狼籍不堪,又觉一阴一户肿一涨,用手一摸,馒头一般。冬梅心中凄然,不想今日采花未成反倒被采了花一心走!思此动怒。见金良那惹祸的家伙偃旗息鼓,遂拾起绣鞋打去。这一打不要紧,正中要害,那物儿又猛虎抬头,威风凛凛起来。
冬梅心中惊异。才刚纳币称臣又要扯旗造反?正思忖间,金良翻身越起,凌空而下扑倒冬梅,将双股架在肩上,挺一枪一又刺。冬梅一阴一中泛溢,突的一声尽一根没入。直捣花一心,喜不自胜。金良一见更不怠慢,奋力冲突,来来往往,又不下五百余一抽一。且下下顶往花一心,一肏一弄不止。
冬梅花枝乱颤,咿咿呀呀叫个不簿。如此煽动欲一火,金良不晓得身在何处,一抽一拽失序,气喘吁吁,如此紧暖娇物,恨不得一口吞下?心下合计之间,又一抽一送两百下有余,渐渐觉冬梅一阴一中春水枯断,遂慢一抽一浅送起来。冬梅亦觉干涩隐痛,知一阴一精一已泄,只是久旱逢甘雨,不忍罢手,遂星眸闪动,勾一引道:“不想你这死贼囚还会耍些手段,弄得我浑身酥一软”。
金良抵住花一心,将舌一尖去一舔一冬梅的香一唇,道:“我的好姐姐,这一招叫老汉推车,老实着哩,待我再弄个手段与姐姐耍一回。”金良说罢,又急急一抽一送起来。冬梅被一肏一得晕去,哪里还知晓金良再耍什么手段,金良见冬梅半晌无息,慌忙拔一出一阳一物,捧起冬梅粉面以口布气,少顷,冬梅才呀地一声缓过气来,断续骂道:“你这死贼囚,不与你耍了,一个老汉推车,就险些要了老一娘一的命,扶我起来吧。”
金良顺势将温香暖玉搂了个满怀,那物儿又直楞楞竖一起,冬梅捻着,不忍放手。金良道:“想必姐姐还要贪吃么?”说罢长拖拖斜躺在地上,冬梅亦不答话,跃身跨马桩入,一婬一水四溢,直直抵住花一心,酸一痒酥一麻妙不可言。冬梅套一弄起来,大起大落,摇摇摆摆,玉一乳一甩来甩去,恣意寻一欢。又手拄于地,旋起圈来,研研磨磨,一浪一叫连连。金良哪见过这仗阵?恍惚之间,龟一头阵阵紧张,遂狂一泄不止。
冬梅觉一阴一中空洞,遂撅一起一臀一尖,见金良那物儿如醉酒的汉子,口中呕吐不停。用手一摸,粘粘一稠稠,与一阴一门落下之物一般。知是他亦泄一了,遂用草纸揩抹干净,穿好衣裙,再看红日都已西斜,燕归巢鸟归林,猛然记起采花之事,慌忙站起。
那金良正躺在上,口里咂咂有声,似吃了琼浆玉露一般,哪里肯起,一只手拉住冬梅玉一腿,一只手摩一弄着一阳一物。冬梅一见怒从心头起,喝骂道:“短命的杀才,小一姐吩咐我来让你采花,你竟躺着不动,都是这般时候了,如何去向小一姐交待?”急得眼泪直掉。
金良这才慢熳坐起,道:“我已采了姐姐一枝花,余下慢慢采吧!”冬梅怒道:“呸,今日让你占了便宜,看我不禀告老爷,将你打死。”金良道:“姐姐敢么?不怕坏了你的名声?还是与我做夫妻罢!”冬梅无语半晌,才道:“老爷那里我可不去说破,只是小一姐那里不可搪塞,早晚要坏事。”金良道:“不怕小一姐见怪。小一姐平素也甚没正经,寻个机会,让小一姐亦嚐嚐滋味,看她还敢怎样?”冬梅大骂道:“呸!也不撒泡屎照照自家,小一姐亦是你碰的!”金嶷支支唔唔道:“我不敢碰自有人要碰,早晚有男人替她破一瓜。”冬梅劈手打了金良一下,道:“那亦轮不到你。”金良一躲,又道:“寻个时机我与姐姐做耍,让小一姐故意看见,小一姐若不动心,我输你一条裙儿。”冬梅道:“亏你想得出!那样小一姐还不打死我俩。”金良摆手道:“你若不信就算了,那花早已替你摘好放在亭子里了。”又涎着脸儿靠了过来道:“姐姐今晚来我处欢娱罢。”
冬梅道:“想得甚美!只此一次。”言罢一抽一身便走,刚走几步,又停了下来,原来一阴一中肿痛举步艰难。金良一旁窃笑不止,冬梅大怒,拾起一枚湖山石朝金良打去,金良捂头落荒而走。冬梅一瘸一拐的寻到花篮,往亭中去寻花束,果见一花盆内有鲜花一束,冬梅忖道:“这蠢才倒有些机灵。”拿了花篮,去回复玉凤小一姐。
正是:
一刻值千金,娇娃欲断魂。
且说小一姐正在绣一锦帕,上面红绿两个鸳鸯交头而眠,见冬梅突至,忙藏至袖中,嗔问道:“缘何如此长功夫才回?”冬梅抹抹眼窝道:“适才小奴去后花园,不慎被一狂蜂蛰了眼睛,故此这般时候才归。”玉凤见她眼窝果有泪痕,便不深疑,吩咐将花儿插在瓶中。冬梅忙将残花从玉一颈瓶中挚出,将新采之花插一入,忙动之中忽忆起方才在后花园中情景,顿时霞飞双颊,心跳如鼓,股间春水汩一汩,身醉神迷,不能自持。玉凤无意瞥见,遂问道:“你又发什么呆?”冬梅忙恢复常态笑容可掬道:“偶忆起园中狂蜂采花之景。”玉凤不解道:“狂蜂采花是自然之事,有什奇怪?”冬梅道:“狂蜂采花,恣意无比。”玉凤道:“你又非狂蜂,焉知采花滋味?冬梅笑道:“奴奴曾嚐此昧,故知。”言罢,忙掩口。玉凤觉冬梅言语甚是奇怪,正欲问个明白,一小厮来到跟前纳头拜道:“老夫人请小一姐过去。”玉凤忙起身款款而去。冬梅伸手劈了自己脸一下,忖道:“今日说走了嘴,小一姐起疑恐难饶过。”见月己上梢头,胡乱吃了些饭食,回房倒头便睡。
这正是: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