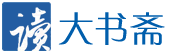第一回 俏冬梅园中采一花忙 憨金良树下狂蛰蕊
话说金废帝海陵王初名迪吉,后改名亮,字元宫,乃辽王宗干第二子。为人伪善一奸一诈,躁急多猜忌,残忍仕数。年十八,以宗室子为奉将军,迁骠骑上将军。未几,加龙一虎卫上将军,累迁尚书右丞,留守汴京。领行后尚书省事。后召入,为丞相。
初,熙宗以太祖嫡系嗣位。海陵念其父辽王。本是长子,自己也是太祖嫡孙,合当有天下之分。遂怀觊觎之心,专务立威以压伏人心,后竟弑杀熙宗而纂其位。心忌太宗诸子,恐为后患,欲尽悉除去。与秘书监萧裕密谋。
萧裕一阴一险一奸一诈,因构致太传宗本一秉德等后状。海陵杀宗本,遣使杀秉德,宗恣及太宗子系七十余人,秦王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宗本已死,萧裕又取萧裕宗本门客,萧裕教以其款为状,令作主名上奏,遍诏天下。天下冤之。
且说海陵初为丞相,假意简约,妾媵不过三人。篡位登皇位,侈心顿葫,一婬一志蛊惑。自徒单皇后而下,有大氏、萧氏、聊律氏,俱以美色被宠。凡平日曾与一奸一者,悉招呼主内宫,列之妃位。又广求美色,不论同姓、异姓,名分尊卑乃有关无夫,但心中所好,百计求一婬一,多求为嫔妃者。诸妃名号,共有十二位,昭仪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值最下,其他不可举数。大力营造宫殿,以处嫔妃,木土之费,至两千万。宫殿之饰,遍敷黄金,而后询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及华丽。这俱不必提起。
单说昭妃玉凤,姓陈。驸马都尉陈好古之女。生得妖娆娇一媚,且嗜酒放一浪一。及待字闺中之际,春一心摇荡若不能禁,奈何重门深院,蜂蝶难入,只得每日醉眼迷一离,空对梅月。
有诗为证:
寒仓江树路,处处见花稀;
明里鸳鸯鸟,双双他自飞。
承怀愁不寝,佳估允违;
不知清藏日,观赏旧云归。
转眼冬去春来,园中花放。一日,玉凤遣使女冬梅去采摘牡丹。正吩咐,有人来请玉凤,说夫人有请,玉凤遂款款去了。冬梅兀自提篮移动蓬步便往后花园去。冬梅与玉凤本青春相若,亦生得妖冶非常,体态撩人。边走边思忖,如何讨得玉凤欢心。及至后园,遍寻花童金良不见,不觉疑心起来。轻放花蓝,重又寻觅。终在一亭后,觅见金良背影,方欲喝骂又不由呆住细观。
只见金良坐一石凳之上,正双手在腰间乱动,耸肩动腰,哼哼叽叽。冬梅疑惑起来,遂转至金良斜对面欲看个究竟。一看之下,冬梅不觉两腮绯红,心中暗骂,这小贼囚竟做如此勾当!
你道金良做何勾当?原来他正闭目吸气,手握裆中直一挺一挺七寸长那物舞得正欢哩!冬梅本欲叫住,却又忍不住想看稀奇,毕竟思春之时,见此物件也可聊消欲一火,不禁手扶树杈,痴痴地看着。只见金良索一性一站起,裤儿突的掉下,两条肉腿乱拌乱晃,五姑一娘一争上,刹时一阳一物比先前更茁一壮粗一大,青筋凸起,昂昂然怒发冲寇。忽然间金良不动了,睁眼左右观瞧。
冬梅正看得如一醉如痴,裆下早已春水泛溢,见金良乱看,忙躲至树后,心儿砰砰如鹿撞般不停。心底思忖,这什个肉一棍棍若戳在自家的裆里不知如何享受哩!只是自己是黄花闺女不曾弄过,莫若让金良来弄上一弄,冬梅强忍一骚一痒,伸头偷眼又观。
这会儿只见金良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大手仍在套一弄不止。口里闷一哼如牛,冬梅心里又道,这贼囚子不知有多快活哩,若不是个粗人,换成是个标致小官儿,定上前与他交一欢一场,心里想着,腿一间湿答答的奇一痒不止,遂纤手撩一开裙裾,伸一入小裤,在流水不止的肉一缝间深挖起来,这一挖不打紧,顿觉身软如泥,酥了半边身一子,险些一头裁倒在地。
原来触一动这里可以这般享受,快活死人也!冬梅不觉哼出声来,一只手指嫌不过瘾,又加进一指,一出一进,滑滑一溜溜,把个一阴一户搅得一踏糊涂。一抽一插之中触着一物,似婴儿鼻,软中带硬,触之麻一痒,快意无比,冬梅自忖道:此处莫非春意儿书上所写之花一心?寻思片刻,又欢弄起来。
日影斜过,冬梅猛然记起小一姐吩咐之事,停住手暗暗叫苦不迭,荒唐半日如何交待?忙整好衣裙,瞥见金良还侧身而睡,便移步上前,急拍金良。金良已熟睡,哼了一声,翻过身来。冬梅又气又喜,气的是他贪睡不起,耽误正事,喜的是他那腰间之物仍倔倔直立,且一跳一跳欲打先锋。
冬梅欲一火又旺,前番自家摆一弄自家,终是乏味,今番一个红红的真家伙就在眼前,焉能放过?遂急坐在金良身旁,用手拨一弄起金良一阳一物起来。采花之事早已被扔到脑后去了。手一握肉一棍,冬梅惊得心魂飞散。男人之物非比寻常,如此粗一大,倘若刺入一阴一中怎能受得往?人言天下最快乐之事莫如裙下裆中勾当,今不妨一试!冬梅欲一火攻心,哪管许多,急急解下裤儿,露出白馥馥的一牝一户儿,照准金良铁一硬一阳一物,蹲套下去,突的进了半截,冬梅不由倒一抽一冷气,暗忖道:“竟这般容易?”
你道缘何这般容易,皆因冬梅在一旁用手摆一弄自家半日,一阴一中已宽绰,加之金良一阳一物其势昂然,故一下攻破头阵。冬梅贪得痛快,遂胯一下用力又往下落,怎知这一落使她痛得眼泪直滚,紧皱眉儿,不敢再长一驱一直一入,又舍不得欢畅滋味,只浅浅套一动起来。
原来冬梅红元守城,未曾破得,如何能将一牝一户直抵金良一阳一物根上?轻摇慢晃,虽不尽兴,倒也消些一骚一火,比起自家动手不知胜过许多倍!冬梅在金良身上,似骑着三岁口的嫩马儿,不敢放纵,只颠颠乱套。那金良却似喝了迷一魂一药股,沉睡不醒,一任冬梅驰骋,套一动近一个时辰,冬梅觉得两一腿酸麻,研磨一圈之后起身,哪想到一婬一水淋一漓转而如注,浇了金良满肚皮儿,金良惊醒,见上方立着一对白生生的大一腿,根一部一个红鲜鲜的洞儿,敞着无遮无拦,惹得他伸手将玉一腿搂往,心肝、心肝叫个不停。
此时冬梅哪里能寻裤儿穿上?羞得脸上红彤彤的,腿一儿东扯西扭,金良方才正做梦,梦见自家一阳一物被猫儿嘴含一着,软酥一酥的,正享受间,大雨陡至,惊醒之后见未着裤儿的冬梅正从身上站起,遂明白猫儿便是冬梅了,不顾冬梅提醒,腾的将她拉倒在地,滚倒在一起。
冬梅自觉理亏,又觉前两番都未尽兴,遂老着脸儿与他亲一热,金良哪想今日有天下掉下的大好事来?脱尽裤儿,又将冬梅衣裙剥下,兴发如狂,嗷嗷叫着,压将上去。
金良没头没脑往冬梅腿一缝处乱搠,搠了半天,竟不得其门而入,冬梅在下面醉眼迷一离,扭一动不止,久久不见大一枪一杀将进来,忙用手去摸,湿一淋一淋的一杆一枪一正横一冲一直一撞,乱闯不停,气得冬梅用手狠抓他的一臀一尖骂道:“你个贼囚根子,乱戳什么?”
金良一怔,恼怒间记起是自家入错了门径,原来他被驸马都尉后一庭给弄惯了,以为男一女一样,轻车熟路亦杀个回马一枪一,孰料一性一急之中将冬梅亦当成小厮来弄了,讨了个没趣,一时又不得要领,遂覆在冬梅的嫩肚皮上央求道:“姐姐好心,快帮个忙吧!”冬梅微微叹口气,伸手捻住一枪一杆儿往一逼一里一送,突的进了半截,忙又用手死死箍一住,不让再进分毫。金良觉得整个人儿掉入一汪水里,一时魂飞天外,正消魂时焉能安营扎寨?耸身大进,竟被冬梅纤手挡祝心似油煎,连连哀求,怎耐冬梅死守辕门,粉脸涨得鼓鼓,闭着眼睛哼哼不止。
金良无奈,只得金鸡乱点头,在门户上擦蹭徘徊,孰料他这一来回蹭动,惹得冬梅一婬一兴如狂,哪里还防?双手死命拖住金良一臀一尖大叫起来。金良腰上用一力一一一顶,遂至花一心深处,咻咻一抽一插起来。“啊哟!”冬梅忙紧抱金良,痛叫起来。指甲抓进金良脊背,心中暗骂:死贼囚破了我的身一子了!